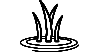
 作者:3672
作者:3672  创建时间:2012-05-14 08:45:00
创建时间:2012-05-14 08:45:00
李孟苏

非遗扎染传承人张士伸给大家展示老纹样

板蓝根扎染的花布没有了
周城村距离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也是大理重点推广的民俗旅游村。村子北端有著名的旅游景点蝴蝶泉——游客们坐大巴到蝴蝶泉,观光约1小时后走出景点大门,先到马路边的餐馆吃大理特产的冰川鱼,再蹩进旅游纪念品商店——它们多数叫“金花商店”,买几件扎染布做的纪念品,10块钱一个挎包,30块钱一套裙装,50块钱已经能买到双人床单了。餐馆和商店都集中在村头、村尾,很少有人往村里走。村里保存完好的古巷道、古寺庙、古照壁、古戏台、“三房一照壁”的白族传统民居、大青树下的集市,没有旅行团的纷扰,很是怡然自得。游客们当然不会注意到村里的主干道其实是富有传奇色彩,带来极大空间想象力的滇藏公路,他们光顾的商店就分布在公路两边。
“璞真综艺染坊”的门牌号是“滇藏路43号”,在周城村17家染坊中规模最大。周城村的染坊多数为家庭作坊,农闲、有订单时才开工,“璞真”常年开工,忙的时候雇了30多人,是我们重点考察的扎染厂。它占据了两进院子,染缸、漂洗池、甩干机、晒架、石碾一铺开,并不显得宽敞。这几天活路少,厂里工人不多,几位中老年妇女有的在往白布上印花,有两位在商店里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往印好花的布上扎花,扎了绳的布扭出一个个的疙瘩,所以扎染也叫“疙瘩染”,古籍中称“扎缬”、“绞缬”,“撷撮采线结之,而后染色。即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其色斑斓”。
几位男工人在染布,用木棒搅动染缸,3口染缸里分别翻滚着黄色、绿色、红色的水,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染好的布泡在漂洗池里,水面上漂着树上落下的米白色缅桂花瓣。这一批活路是裙子,一条条染好、漂洗过的裙子挂在晒架上晾着,五颜六色,也有蓝色。“这不是植物染料染出的蓝色,而是化学染料染的。植物染料染出的蓝,蓝里带翠;化学染料染出的蓝发黑。”随队的民间工艺专家宁成春说。宁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之余,长年研究民族手工艺,曾在江浙一带长期考察蓝印花布。
传统上,周城村扎染用板蓝根制成的土靛,也叫“湿靛”。白族文化、扎染专家,云南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少萍介绍说:“白族聚居的大理洱海地区是云南纺织文化的摇篮地之一,在东汉时期已形成完整系统的染织法。据《新唐书·南蛮列传》记载,唐贞元十六年(800),南诏舞队到长安献艺,所穿舞衣‘裙襦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革’光彩照人,即为扎染而成。具体到周城村,其扎染历史到目前没有找到文献明确记载。据调查材料,周城村的扎染约始于明末清初,是从四川传来的,历经了300多年的发展。到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全村除种田外,兼营同一种手工活,有的村专营棉花,有的专门纺布,有的专门染布,有的从事裁缝,还有的制作木纺车。在这个时期,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活路精细,脱颖而出成为远近闻名的织染村,后来被文化部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首批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就成了扎染的代名词。”
周城村的扎染出名到什么程度?周城村村委会副书记段树生说,当年大理一带的女孩子出嫁,嫁妆里一定要有周城村扎染布做的衣服、头饰、床上用品,不然就很没面子。“文革”期间,扎染作坊几乎全部被毁,但还有人甚至是县里干部偷偷拿着白布到周城请工匠私下染布。
“璞真”的厂长段树坤30多岁,少言寡语,迎来送往的都是他媳妇段银开。段银开32岁,从七八岁开始做扎染,现已是白族扎染技艺的云南省级传承人。她戴白族头饰,穿本民族的白色小褂、桃红色绣花坎肩,搭配的却是喇叭裤和高跟鞋。段银开坦率地说,他们厂里现在用的不是植物染料,“村里现在几乎家家染坊都用化学染料。只染单一的蓝色,卖不掉,很多游客认为板蓝根和化学染料没区别,嫌蓝色太单调,不鲜亮,还嫌弃它褪色。化学染料上色好,颜色多”。院子里有几个大木桶,那是土靛染布时用的桶,已经被渗透木板的板蓝根染成了蓝色。现在它们也用不上了,箍桶的铁丝全锈了,只做招牌用。
还种板蓝根吗?“种了一些,在那儿。”段银开指着墙根一个小花圃,砖头围起的地里种了几十株。“来厂子里买扎染纪念品的游客总要问板蓝根长什么样子,我们就种了一些。这么少,不够染布的,也就是观赏。我们平常喜欢用板蓝根叶子泡水喝,清热,‘非典’的时候,游客把我们种的板蓝根都挖走了。”段银开说。
只有张仕绅还会用板蓝根做扎染
一位老人进了“璞真”的院子,穿过院子里的一排扎染成品时,他随手指着一块布说:“这树叶花没扎好。”他笑眉笑眼,穿件自家缝制的蓝布褂子。宁成春小声说,这件褂子肯定是土靛染的,年头应该不短了。一问,果然有40年了。“这布是我自己用板蓝根染的。”老人说。那蓝色经过无数次洗涤,显出沉稳、温润的色调,凝重雅致。老人叫张仕绅,虚岁70,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是白族扎染技艺。
张仕绅是被村委会叫来的。他家祖辈从事扎染,是周城村最好的手工艺人,云南唯一一位国家级扎染传承人。他给我们分发名片,名片上的手机号码是“139”打头。“我是中国最早的手机用户。”张仕绅骄傲地说,那时他担任村办企业大理周城民族扎染厂的厂长。他说,1987~1996年,他当了10年厂长,把厂子经营得红红火火,产值最高的一年达800万元。在恶性价格战中,2004年厂子倒闭。“璞真”所用的正是当年“民族扎染厂”的厂房,张仕绅指着院里那栋3层办公楼说:“这是我当厂长后第二年盖的,那个年代就花了30多万元呢。现在卖了,跟我没关系了。”
他说,他有10多年不碰染缸了,厂子关门后,他回家养老,每天侍弄家里园子。他家在坡上,距离周城村北边的本主庙——灵帝庙不远,“文革”前庙里曾供奉有染衣业祖师葛洪、梅福二仙的塑像。要么他就去棋牌室打牌,要么去帮姑娘(大理方言,“女儿”之意)照看商店。张仕绅给他的三个姑娘每人开了一家商店,都在滇藏公路边,其中两家也叫“金花商店”,卖白族服饰。他的大儿子张人彪开了家染坊,他也不过问。问为什么不做扎染了,他答:“现在的扎染都用化学染料,不用植物染料,没意思了,我也老了。”张仕绅笑呵呵地说,他曾经保护了周城村的板蓝根,使之躲过了灭绝之灾。
板蓝根原本在苍山上野生,用量大了后,染坊人家就在山上进行大面积人工培育。张仕绅介绍:“板蓝根每年二三月下种,8月底、9月初收割,留下根,只割叶和茎,按比例加石灰、水,在松木缸里泡一周。泡制过程中每天要用染棒捣打,让水起泡,再沉淀、上架、去渣,反复几次,水分蒸发掉,蓝靛就做好了。手艺好的人100斤板蓝根能出30斤蓝靛,手艺差的也就出十五六斤。做得好的染料只要拿清水泡着,不脱水,可以用10多年。”周城村历史上也是云南重要的土靛产地,生产的土靛在大理和周边的洱源、巍山、剑川很畅销,还远销到弥渡。
“苍山十九峰,峰峰有水。”周城村水资源十分充足,张仕绅回忆他小时候,村里有300多户人家做扎染,苍山上的溪水流下来,染坊人家便在门前支起木制的大染缸,用活水漂洗经板蓝根染过的布匹。1949年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发生变化,周城村几乎没有人种植板蓝根、染布了。1961年,19岁的张仕绅因为是“高小”毕业生,到大队当了会计。此时政策有松动,大队恢复了板蓝根种植、土靛生产和扎染。“当时周城村分4个大队,别的大队做土靛都做垮了,只有我们大队有个懂技术的老倌才做得好。我们卖板蓝根染料,100斤能卖50元。”随后“四清”运动开始,“上面派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队给土靛泼上大粪,要集中销毁。我和队长、技术员晚上扒开大粪,偷了100多斤板蓝根渣渣(土靛),悄悄保留下来。一两年后工作队走了,我们又开始悄悄搞板蓝根,最多也不过种十来亩”。
1983年之后,大理逐渐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传统民艺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急速解体,工业商品对传统市场进行了无情的占领,扎染变为旅游和外贸商品后,工匠们在迎接发展机会的同时,毫不犹豫抛弃了传统,抛弃了板蓝根染料。
宁成春说,扎染的韵味在于蓝、白二色之间的自然过渡。由于扎花时针法有松紧,浸染时程度不一,染出的每块花布都独一无二,加上用植物染料后略有脱色,色彩的对比淡化,反差趋于缓和,从而透出朦胧、柔和美。张仕绅、段银开、段树生等人则介绍,板蓝根有药性,染过的服装、被单有消炎清凉的作用,对皮肤好。“我们这里的人生了疮,被蚊虫咬了,就用染缸里的板蓝根水洗皮肤。”张仕绅说,80年代日本客商来厂里考察,问染料是不是纯植物的,他情急之下从染缸里舀起一瓢蓝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可现在“村里会弄板蓝根染料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周城文化站的杨麟站长在一旁说,这老倌舀起一瓢水,看一眼、闻一闻就知道这缸染料好不好。宁成春认为,民间工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具备手工艺尊重自然的本质,正宗白族扎染的核心价值在于三个元素:手工扎花,采用天然的板蓝根染料,手工印染。他说:“板蓝根染料环保无毒,不用它了,白族扎染又和工业化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周城村的扎染作坊早在民国年间就开始用洋靛,洋靛算云南省大宗的进口商品,市场份额最大的是印度的月亮牌、德国的公鸡牌、瑞士的狮马牌。洋靛的大量倾销早就开始冲击土靛生产和市场,据1988年出版的《白族简史》中记录:“洋靛的输入,迫使大理周城、喜洲一带的土靛染布业逐年减少,土靛生产逐年下降。”张仕绅、杨麟等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辈人回忆,他们小时候并没有见过洋靛,洋靛第二次冲击周城作坊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白族扎染是热销的外贸商品。云南省工艺美术公司、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找到张仕绅,要他打几个样品,帮他们吸引来日本客户。“我并不愿做外贸,自产的板蓝根染料自己用都不够,哪里再顾得上出口?纺织品公司的一个经理拿来进口染料,是瑞士和德国产的,说进口的染色快,让我们把土洋两种染料混在一起用。”洋靛大大简化了工序,上色稳定,色彩丰富,最重要的是降低了染布的成本。于是,化学染料迅速风靡开来,替代了土靛。原来衡量一个作坊的规模会说它有“几个染缸”,现在这种说法也成为过去。
段银开说:“除非是客户订单要求我们必须用植物染料,一般的产品都用洋靛。用土靛成本太高。”张仕绅和段银开估算,土靛染布的成本比洋靛至少高5倍。板蓝根染料比化学染料成本高,高成本主要体现在工艺上。用土靛做扎染,是以冷染的方式浸染,反复多次才能成色。张仕绅告诉我们,土靛染色“少则三四天,一般要用一周,反复染20次以上,每次都要染色、氧化、漂洗三道工序,出来的颜色还不一样,而且染缸对工人的要求很高”。在张仕绅家,他拿出一件长袍,是他给自己准备的寿衣。他说,“布料是40年前自己染的,用了两周才染好”。化学染料则是煮染,一次就能成色,还不脱色。段银开也说:“土靛染布褪色,顾客不喜欢,还有人投诉过。”张仕绅的寿衣布料蓝中泛红,他介绍“这是猪血的红色,我用了猪血固色”。周城村的老手艺人用猪血、牛皮胶为染好的蓝布固色,减轻了褪色的问题,但也增加了成本和难度,仍然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求。
土靛种植户也不愿种植板蓝根。种板蓝根的田间劳作非常艰辛,泡制土靛时间长,对经验和技术要求高,稍有不慎整桶染料全部报废,风险很高,但制好的土靛一斤才卖几块钱。2000年,周城村背后的山上还种了100亩板蓝根,是几户人家的责任田,由期望守祖业的老人们种植,现在几乎没有成片的板蓝根田地了。有人乐观地称,目前植物染料只占到市场不到1%的份额,潜力非常大——在周城实地考察后发现,这个结论未免下得过早。
全面使用化学染料,对环境污染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周城村地势西高东低,村落与洱海之间是倾斜的农田。每天,扎染作坊排出的红、紫、蓝、黑、绿的刺鼻污水就顺着倾斜的地表渗入农田。如果天逢下雨,污水直接流向洱海。有三五个雇工的小作坊每天排污量约为1吨,大作坊就无法估计了。污染引发了染坊个体户和村委会、其他居民户之间的矛盾,对此,村委会副书记段树生表示无奈:“我们也请过专家希望解决问题,专家说要治污必须建污水处理厂,治污成本1立方米污水花1块钱,买设备要120万元。村里的17家个体户不愿出这笔钱,村委会也没钱,村干部的工资都是贷款发的。”曾有居民向州政府举报污染问题,村委会夹在中间很为难。“如果我们真的严格执行整改条令的话,这17家作坊都得全面停产。难弄啊,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扎染传承的困境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柳宗悦周游日本列岛,对日本民族手工艺做了全面考察后,不无忧伤地发现,摧毁手工艺的不是战争,而是商业化。商业化导致民艺品的生产过于依赖机械作业,“有着使世界产品同化的倾向,往往被用来逐利”。
半个多世纪后,周城扎染进入了大工业环节,也走进了日本民艺当年面临的困境,其中一个困境是优质的传统产品得不到尊重。段银开的库房里还存有板蓝根染的产品,是集体厂在80年代的产品。它们蓝得温厚,图案繁美,一条双人床单要200多元。“没人买,嫌贵。”段银开说。
商业化滋生了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竞争。周城村扎染市场的竞争还处于初级的无序阶段,各作坊主以压低成本为主要的竞争手段,这破坏了周城村的扎染生态。除了个体家庭作坊,1983年周城村成立了大集体性质的蝴蝶牌扎染厂,后来张仕绅将其改名为大理周城民族扎染厂。村里扎染最繁荣的时候,仅承担扎染厂外包扎花业务的本村和周边村民就超过5000人。集体企业有专职图案设计师,对周城扎染的创意改革做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见到了图案设计师,他叫董维水,是张士绅的外甥。董维水40多岁,见人很腼腆。张士绅很赏识这个外甥:“他是高中文化,读书时跟本地的画家学过画画。他还懂木匠,会造房子,会扎染桶。全村只有他一个男人会扎花。”扎花特别要求细心和耐心,向来都是女人做,董维水会扎花在村里也就有了轰动效应。他的扎染手艺是跟舅舅学的,厂子破产后他回家自己做染坊。董家染坊在村里规模中等,只有农闲和有订单时才开工。
在董家院里挂了件男式夹克衫,上面有扎染出的抽象图案。“这是我的衣服,自己扎着好玩的。”董维水说。他搬出几大本影集,里面有1000多张照片,有厂子当年为日本、东南亚客户加工的产品的图形,也有他自己设计的花样,“大约230多种吧”。他还保留了30多种扎染用布料的样品,是非常有心的人。白族扎染的传统纹样经过“四清”和“文革”,流传到80年代只剩下小梅花、小蝴蝶、毛虫、马齿4种,董维水将纹样发展到10多种,其中有种蜘蛛花,最受订户认可。他和厂里的艺人们还开发出30多种扎花的针法。以这10多种纹样、30多种针法为基础,组合排列,董维水设计出230多种图案,“可以扎出任何图案,除了花卉、动物,还有文字、人像”。我看到一张照片,是一对日式门帘,河水在蓝布上流动,他介绍说这是用毛虫花变形扎出的。
张仕绅无奈又有点生气地说:“村里现在任何一家扎染用的图案,都是我们厂里搞出来的,他们偷去了。本村人,也不好追究。”扎染最关键的步骤是扎、染,扎花工序是外包出去的,这样集体厂里开发的新图案、新技法完全处于泄密状态。本村、外村,甚至整个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个体染坊学到新设计、新工艺后,彼此展开了激烈而恶性的竞争,导致市场环境越来越恶化。扎染厂遵循严格的质检标准,没有偷工减料之说,报废率高;个体染坊推出和扎染厂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质量、价格却低很多。在税收上,个体户只需缴纳4%或6%的定额税,大集体性质的扎染厂却要交17%的增值税,成本远高于个体户。扎染厂倒闭后,没有了专业设计人员,扎染工艺再无创新,专利更得不到保护,个体户几乎是滥用图案、技法,推出的产品千篇一律,并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低价让扎染产品廉价化,板蓝根染料被淘汰正是廉价化的最突出后果。
张仕绅等周城村的老辈人认为,扎染丧失了经济优势,无法留住技术人才,越发倚重廉价的劳动力。董维水就说,他家做扎染的经济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搞旅游、搞工程的差远了”。段树生介绍说,周城村的建筑工匠闻名省内外,用鹅卵石铺路面的手艺很有口碑,外出打工的周城村人多数从事这一行,“那些包工头挣的钱就不是开扎染坊能比得了的,扎染搞得好一年顶到天挣10万元”。扎花的快手、好手一天收入10块钱,慢手两三块钱,而扎花不仅是技术活,还是力气活,扎久了手指关节变形。所以,手艺好的人都愿意出去打工,就连老太太也宁愿去旅游点的餐馆洗碗,一天能挣30块钱。现在做扎花的都是要领小娃娃,被家务绊住脚出不去门的妇女,并不情愿做扎染。年轻人不愿做扎染,技艺传承给谁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对此表示担忧:“传统手工艺是在相似的生活形态下才得以代代传承的,人是这传承中的主角。民间艺人的流失成为民艺发展的严重问题。”
张仕绅的好手艺也传不下去。白族扎染自古传男不传女,张仕绅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大理的银行工作,大儿子张人彪原来在村里医务站当郎中,后来自己搞了个染坊,也是用化学染料的。“他不行!”——张仕绅没有多说儿子的情况。侧面一打听才知道,爷俩彼此不认同对方的思路,分歧很大。一位染坊主人告诉我,张人彪发明了“注射器染色法”,用针管给扎好的花“打针”,其实是套染,可以给一个图案同时染出5种颜色。传统的染法因为染料渗透的程度不同,特有一种色晕,套染后没有了色晕,张仕绅显然不欣赏这样的创意,索性不过问儿子的生意。他说,当年扎染厂曾举办过14期扎花培训班,培训了2000人次,对周城扎染的传承和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都是家庭作坊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要发展、传承扎染手工艺不成规模不行,必须再次建厂。“我要是自己搞扎染,那不得了,这些人都算不上。”老先生看着他家照壁上“百忍家风”4个大字说。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