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民俗学论坛
来源:民俗学论坛  作者:江帆
作者:江帆  创建时间:
2019.05.13 09:33:00
创建时间:
2019.05.13 09:33:00
摘要: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以口述形式承传的一种族群记忆,其内容的建构与播衍蕴含着丰富的族群历史与文化变迁的细节与因素,不仅是满族及其先民对其所直观感知的族群历史以及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也是满族根性文化的重要遗存,体现着雄阔遒劲的“史书”、“史笔”风格与蛮荒古朴的叙事特色。满族说部在传承与播衍方面具有封闭与单一的特点,但也与其他类口头文学一样,受社会发展变化及传承人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的变异。
关键词:满族说部;生成;播衍
作者简介:江帆(1958-),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东北区域民族与文化、生态人类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学及传承人研究。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口承叙事与社会记忆的最初发生,实为这一特定的人类群体对其所直观感知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人的行为和所处的时空背景相互作用,相互阐释,从而生成口承叙事的意义以及族群社会记忆的内涵。法国学者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曾经指出,各个民族不管他们的种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在自己的发展中,总会碰到极端相似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总得为满足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而采取同一的生产方式。口承叙事的创作与承传,便属于人类的一种“精神的需要”,这种“精神生产”,无一例外地都会带有其“种源和地理环境”的印记。在文字和印刷术没有普及的时代,人类知识与经验的传承主要通过口头叙事的形式,以口耳相传延续成族群的记忆。这种现象,在许多民族与族群的文化传统及民俗知识的传承中都有生动体现。满族说部,即是满族及其先民以口述形式承传的一种族群记忆,它不仅是满族及其先民对其所直观感知的族群历史以及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也是满族根性文化的重要遗存。
一、满族“讲古”的传统与“满族说部”的生成
历史上,由于满族及其先民创制文字较晚,应用文字的时间和范围都有限,因此族群文化的传承和生活习俗的沿袭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形式。口承叙事曾是满族及其先民进行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和典型形式。
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前,几乎没有以文本形式记录本民族历史的习惯。与许多不发达民族一样,满族及其先民记录历史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氏族部落酋长或萨满来口传历史。满族在其先世女真时代即有“行歌于途”、“自叙家世”的习俗,对此,我国一些典籍有所记载。如《太平御览》记载,满族先民自古“无文墨,以语言为约”。《金史》记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可见,其时金国国史的构建都要依靠口传传统。在满族民间,人们习惯于将这类讲述活动称为“讲古”或者“讲古趣儿”、“讲瞎话儿”。讲古以敬祖、颂祖、祭祖为主要内容,对满族民众来说,讲古不仅仅是娱乐活动,而且是进行族教、祖训的重要形式,带有庄重的宗教色彩。满族民间讲古习俗的传统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始终为满族民间喜闻乐见。从人口繁多的城镇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偏僻山村,只要是满族聚居的地方,或一个部落,或一个村屯,或一个姓氏(满语称哈喇 hala),常有讲古活动。讲古的时间,一般在丰收后的农闲季节,或在新春正月。那些时间,合族聚会,或续谱,或办红白喜事,或祭祖跳神等,诸事操办完了,晚上的余兴多是讲古活动,常常是男子一伙,妇女一伙,有时合族听讲。开讲时多由噶珊达(村长)、穆昆达(族长)或者德高望重的一户之长主持。众人先请年长者讲唱,然后依序请在座的长辈讲古,每人可自定故事,内容、数量不限,可长可短,可夹叙夹唱,讲到兴头上,也可以载歌载舞。讲述人一般都选自己最精彩的故事,各献绝艺,各吐所长。这样,在各姓氏中都产生了几个聪慧博闻的故事家,他们多受本族穆昆达或家长的传授,通晓本族的历史传说,谙熟讲故事的技巧,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爱戴。他们经过长期实践的锻炼,讲得更加娓娓动听,滔滔不绝,以至代代相传,涌现出或一姓或一家的讲古传承人。如已经出版有满族故事专集的著名民间故事家傅英仁、李马氏、李成明、佟凤乙、姜淑珍等,都是其家族的讲古传承人。在满族使用本民族母语——满语的时代,满族民间讲古主要包含两大类别:一是广泛流传于满族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和谣谚等短篇口头叙事,即人们寻常所说的“故事”或“瞎话儿”;一是具有独立情节和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恢宏的长篇叙事,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满族说部 ”。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黑龙江满族聚居地的一些老人在生活中还袭用满语,“故事”与“说部”在满语中有着严格的区分。满语一般将故事称为“朱伦”(Julen)或“朱奔”(Juben),意思是讲“瞎话儿”,讲“古趣儿”,具有无拘无束的随意性,听故事的人座次也不必严分辈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对于讲颂族史家传的长篇“说部”叙事,民间则称为“乌勒本”及“德布达林”。赵志忠在《清代满语文学史略》中提到:“德布达林(debtelin)是满族说唱文学之一,德布达林的满文原义为‘本子 ’,即说唱故事或长篇说唱。这种说唱本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莉坤珠逃婚记》,又称《琛鄂勒斗莫日根》。”德布达林指满族民间比较古老的叙事诗,因流传时间久远,遗存较少,故而在满族民间流传并不普遍,其影响远不如“乌勒本”。乌勒本(ulabun)为满语,意为“家传”、“家史”、“讲古”、“英雄传”等,是由满族及其先民创作并传讲的一种反映历史上满族氏族社会征战生活与情感世界的长篇散文体或韵文体口承叙事。
乌勒本最初是以口头形式产生的,讲唱的内容全凭记忆,初时人们在木头、兽骨、动物皮毛上刻镂一些简单的形象绘画以及以堆石、结绳等方法作为辅助记忆的手段,备讲唱时望图生意,看形想事,观画联想。至清代,满族拥有了本民族的文字,尤其在与汉文化广泛交融,通习汉文之后,讲唱乌勒本时才出现了以满、汉文字混杂记录的讲述提纲。
清代初年,满族民间讲唱乌勒本盛行,其时的乌勒本包括用满语讲唱的所有叙事书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明代嘉靖、万历年承袭而来的大量汉族文学读本,这类文本被翻译成满文后,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满族民间广为传讲,及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满族聚居的东北乡间还可见到线订的这类手抄本。还有一类便是在石、木、骨、革上绘成的符号或神谕,以及或用满文,或用满汉文混杂,或用汉文抄写的属于“族史”、“家传”类的“满洲书”,满语叫“满朱衣毕特曷”。这类满洲书是满族各氏族家藏神品,倍受尊敬。在古老的时代,满族各氏族几乎都有记述本族族史家传的乌勒本,同时也拥有能够讲唱这些乌勒本的名师。诸望族大姓纷纷将具有“说史”和“唱颂根子”性质的乌勒本视若家珍,甚至推崇到神秘、肃穆、崇高,令人敬畏的地步。不仅各望族大姓皆以拥有乌勒本而互炫荣耀,就是寻常个体民众也往往因据有乌勒本而赢得全族的尊重和拥戴。对于满族各氏族来说,讲唱说部是非常隆重而神圣的事情,说部内容是赞颂本氏族历史及本氏族先祖的英雄业绩的,有严格的史实约束性,不允许隐饰,更不允许胡编乱造,是族史、祖史,是对祖先虔诚的赞颂,因而讲唱者并非寻常的“朱伯西”(讲述一般故事者——作者注),多为本氏族中的萨满、穆昆达或德高望重且有文化的老人,并且只能在一定场合、一定氛围和一定时间里讲唱。通常,满族一些望族人家,在逢年过节,举行家祭、族祭之后,一般都设有这样的环节:招亲朋故交,凑到一起,专请色夫(满语,师傅——作者注)来讲上几段过瘾的满洲书。讲述说部的环境庄严而肃穆,具有严格的内向性特点,弥漫着宗教的气氛。听者按辈份依序而坐之后,讲述者先要肃穆地从西墙祖先神堂上请下祖宗匣子,里面装有在石、木、骨、革上绘成的符号或神谕、谱牒等,焚香、祭拜,进而梳头、洗手、漱口,方可讲述。讲述完毕,还须肃穆地将神谕、谱牒等送回西墙上祖宗匣子里妥善保存。今天我们指称的“满族说部”,主要就是指这类讲述活动的内容。
自20世纪初开始,满语渐废,东北满族民间渐将乌勒本改称“满族书”、“家传”、“英雄传”等。因其体式与汉族民间的“说书”比较接近,每部可独立讲述,后来便统称“说部”。目前在东北满族中,提及乌勒本,或许仅有少数通晓满语的老人知其为何物,此外便只能在满族一些姓氏保存的谱牒和萨满神谕中见到这一词语了。
关于满族“说部”的概念,近年来学术界也有界定,笔者比较赞同学者高荷红的观点:满族说部是乌勒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称呼,它沿袭了满族“讲祖”习俗,是乌勒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既保留了乌勒本的核心内容,又有现代的变异。最初在氏族内部以血缘传承为主,后渐渐地以一个地域为核心加以传承。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满族各氏族祖先的历史、著名英雄人物的业绩、氏族的发轫兴亡及萨满教仪式、婚丧礼仪、天祭海祭等。篇幅简繁不等,少则几千字,多则几十万字。原为满族民众用满语讲唱,现多用汉语,以说为主。它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长篇叙事诗等形式被民众保留下来,是韵散结合的综合性口头艺术。

有关满族说部的内容构成,目前,国内媒体及学术界基本采用满族文化学者兼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先生依循满族说部的传统,以“类化”方法,对满族说部进行分类。富育光先生将满族说部划分为四大种类:
1.窝车库乌勒本,即满族一些姓氏的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远古神话与历代萨满祖师们的非凡神迹与伟业,俗称“神龛上的故事”。窝车库乌勒本,主要来源于各姓满族珍藏的萨满神谕及萨满的重要遗稿与生平记忆。如爱辉地区流传的《音姜萨满》(《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恩切布库》,黑水女真人创世神话《天宫大战》,流传在乌苏里江以东锡霍特山麓的东海萨满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便是典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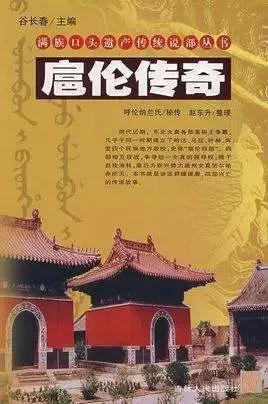
2.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近二十余年来在满族诸姓中发现较多,主要有:吉林长春市满族赵姓家族的赵东升先生承袭祖传记录的《扈伦传奇》;四川成都井巷子满蒙学会刘显之先生记录的《成都满蒙八旗史传》;黑龙江依兰镇满族里门德哈拉后裔李克中先生讲述的《三姓志传》;黑龙江双城县满族政协委员马亚川先生承袭的《女真谱评》《海宁南迁传》;黑龙江爱辉地区富氏家族承袭的《顺康秘录》《秋亭大人归葬记》与《东海沉冤录》;黑龙江宁安地区傅氏家族承袭的《东海窝集部传》等。《萨布素将军传》《忠烈罕王遗事》《雪山罕王传》《顺康秘录》《东海沉冤录》《东海窝集部传》《成都满蒙八旗史传》就是比较有影响的“包衣乌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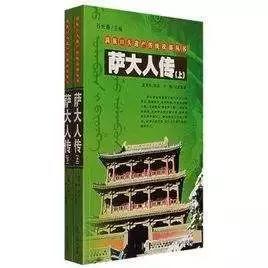
3.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这部分满族说部内容也很丰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一是历史传说人物的演义。真人真事的传述,如黑龙江宁安地区富察氏满族后裔傅英仁先生承袭祖传讲述的《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爱辉地方富察氏满族后裔富希陆先生承袭祖传讲述的《萨大人传》等。历史传说人物的演义,如《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金兀术传》《忠烈罕王遗事》《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鳌拜巴图鲁》《松水风楼传》《黑水英豪传》等。
4.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故事。这部分满族说部主要以各氏族长期流传的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为主,演述文本有韵有白,主要作品有:著名的镜泊湖爱情传说《红罗女》以及有关红罗女的说部系列,包括《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等;歌颂保佑出入图们江口渔船平安的守航江神的《图们玛发》和歌颂护卫满族众姓福祉的萨满的《关玛发传奇》;讲述地方风物传奇的《巴拉铁头传》。此外还有《西林色夫》《恩切布库》《白花公主传》《姻缘传》《莉坤珠逃婚记》《依尔哈木克》《得布搭力》等。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多维对话中形成和逐步完善的,蕴含着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内涵,折射着满族及其先民对东北区域历史和自然环境的独特认知与生存体验,体现着满族民众特有的生态思维与哲学思想,对于与“绝域”生存环境抗争的满族社会发展史,有近乎全景式的展演,是对人类生命意识的艺术展现与诗化歌颂,同时也是满族民众在生存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在其日常生活中,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尤其那些讲颂族史家传、带有族群“根子”印记的说部,就是对满族一些支系族群的生存史与文化史的艺术书写。
二、满族说部的内容构成及其特点
满族说部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以满族特定的族群历史与生存环境为背景组成的,满族说部集中地反映了满族一些支系族群的生存史与文化史,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表征,也凸显着“种源和地理环境”的印记。透过满族说部叙事的幽深长廊,我们可以发现负载与传承这些叙事的满族民众古往今来经由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心路。
早在商周时代,我国东北区域已有满族先世肃慎人生息繁衍。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窝稽说》记载:“今辽水东北尽海诸地……皆称窝稽,亦曰乌稽,亦曰渥集、阿集。”据《后汉书》《晋书》等记载,这一区域“东极大海,广裹数千里”。《满洲源流考》又记:其地“负山襟海,地大物博,又风气朴浮。”《大明一统志》记强,其域“东为‘野人’女真”,“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东海女真栖息的地带,自远古直至近代始终是世界范围内分布最辽阔、形态最完整的渔猎文化区。渔猎文明的出现是栖息于这一区域内的—些古老的族群对当地自然生存环境适应的结果,而渔猎文明在这一区域的绵延不绝,又托庇于当地远离历代社会文明中心的社会环境。
满族世居的我国东北地区的地理有两大持点:一是相对隔绝,二是自然资源丰饶。满族先民崛起的“白山黑水”地区位于北纬40度以北,地处北温带。这一地区的北部,是一望无际的外兴安岭和西伯利亚荒原,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寒冷的气候使人难以逾越。极地湿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大高原肆虐南下,却被阻挡在外兴安岭以北。在外兴安岭南面,形成了植被茂密、草肥水美的丘陵平原地貌。区域由于纬度较高,冬季漫长寒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仅不能耕种、放牧,甚至人类都不适宜长期户外活动。同时,在嫩江流域,又广布着亚洲较大的沼泽地区。茫茫林海,皑皑雪原,坑洼相间的沼泽地,构成了独特的东北地区自然景观。东部和南部是鄂霍茨克海和西太平洋,对东北又形成天然的屏障,西部是万里的蒙古戈壁。东北区域的自然气候的共同特点就是寒冷,特别是位于北纬 50 度线附近的吉林和黑龙江广大地区,显得尤为突出。这一生态区位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资源等生态条件与环境,从根本上规约了区域内所有族群的生计方式及其文化的建构与衍化。
《乌布西奔妈妈》《东海窝集部传》《女真谱评》《东海沉冤录》等说部,对满族早期社会的天灾、人祸、瘟疫、瘴疠、兽害等有着大量生动而又具体的描写。兹随便择举一例,《东海沉冤录》曾这样描述:
那是个秋分时节,辽东遍地洪水,江河泛滥,东海窝集部居住地的大小沟谷满了水。乌苏里江江面宽得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汪洋,白茫茫的,兴格定亦变成了小海。由于江水浩荡,致使庄稼被毁,野兽大多被淹死,人们既没有粮食吃,又不能打猎。部落与部落间被洪水阻隔,无法联系,难以通达信息。乌蛇岭一带比其他地方遭灾尤甚,更加空寂、凄凉。洪水淹没了一个个小山包,有如十几个小岛相互隔绝着,被困的族众只能用歌声表达心意。秋末,大水退下去了,族人却染上了山达哈(天花),整个东海人死亡不计其数。那时是天天在死人,有的岛子几乎全都死光了,尸骨臭气熏天。灾难同样也降临到赫思痕部,为了生存,阿济格赫思痕妈妈即小赫思痕妈妈只好率领仅剩的百十号人,沿绥芬河上游往西逃,一路仍不断地有人倒下。到了喜扎河口索玻克山和鄂利哈山交界处时,由于谷深林密,参天的大树像擎天的柱子一般遮天蔽日,致使族人迷失了方向,转来转去,怎么都无法走出密林。本来就是带病的躯体,再加上无水、无粮,奄奄一息的人们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答,眼看兴旺的赫思痕部将要灭绝在这片阴森无情的原始森林之中了……
类似的描述在那些讲述族史家传以及先祖英雄业绩的说部中大量散在。不难想象,对于世代生息繁衍在如此生存环境中的满族民众来说,只有在身体和精神上都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才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生存活动。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满族自先民时代即已形成了一些带有共性的族群体态特征和性格特点,即身体强壮魁伟,沉敏罕言,勤奋、吃苦、耐劳,有坚强的意志和韧性,能够承受困难和打击,能够抵抗各种外在侵扰。不难想象,与相对成熟的农耕生计相比较,持渔猎生计的满族先民注定要承受更多的危险与风险。农耕生计可以带来剩余的食物,使农耕民获得闲暇休息,而狩猎生计只能让人不停地突逐奔波,不停地搏斗厮杀,唯有如此,才能保证食物不中断。原始的狩猎是极其残酷的,虽然满族先民已经拥有了尖锐的猎器,并且是群攻猎物,但每一次狩猎都几近于一次动物间的博杀:猎人能吃到鲜美的肉,但稍不留意也能变成猎物口中的美味。正是数不清的血腥厮杀,铸就了满族民众勇敢、坚强、剽悍、善战的群体性格,这种群体性格不仅体现在日常的狩猎生产活动之中,也显见于满族共同体内部各部落之间的争战以及对邻近民族的掠夺与讨伐战争中。如《后汉书》记载:“挹娄国,众虽少,而多勇力。又善射,发能人目。”“善射中,人即死,邻国畏其弓矢。”《金史》记载:“渤海人三人抵一虎”,“女真兵一过万将无敌于天下”。《朝鲜实录》记载,女真人“勇于战斗,喜于报复,一与作隙累世不忘。满族先民不仅勇猛,而且还极具耐力,“女真人善射,耐饥渴苦辛,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过。”满族民众将这种文化个性视为同尖石利器一样重要和宝贵的文化财富。历史上,在满族先民从氏族向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以及部族的过渡与进化过程中,族群内部各支系可谓连年征战不断;在满族同体内部实行了集团化和组织化之后,满族先民更是频频地对邻近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发动掠夺战,靠战争掠夺所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比靠原始的渔猎生产所得的经济利益高得多。“久而久之,这种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就硬化成一种习惯,以致在人们看来,‘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这种如尖石利器一样的文化个性,当是满族文化的精神内核所在。当然,满族文化深层结构的这种特点,是历史上满族及其先民所处的族群生存环境铸就的。
满族说部的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满族及其先民的社会生活以及族群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历史事件,体现着雄阔道劲的“史书”、“史笔”风格与蛮荒古朴的叙事特色。可贵的是,在满族说部宏大的叙述中,散缀有众多的细节点染,包含着大量的从未付诸文字的珍贵史料,生动而艺术地再现了满族氏族部落的发轫兴亡、聚散迁徙、征战结盟、蛮荒古祭,以及族群生活中的开拓创业、风土人情、英雄史传、社会风貌等。取材于遥远时代的《东海窝集部传》,便以近乎写实的手法,以东海窝集部的单楚和先楚两兄弟的坎坷命运为轴线,以小见大地再现了满族先民社会在勿吉时代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整个过程。《女真谱评》则从九天女与渔郎成婚,繁衍女真族讲起,一直讲到阿骨打完颜部的勃兴、辽金大战、金朝鼎盛以及清朝的兴衰,几乎囊括了满族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堪称一部由满族人凭脑记忆、用口传承的满族社会的兴衰史。《东海沉冤录》讲的则是明代东海女真各部落被乌拉部征服统一的历史故事,其间充满了战火与血泪,是一部东海女真人秘传的哀痛心史,同时也细腻地描写了大量东海女真人特有的古老习俗和原始古朴的价值观念。《萨大人传》与《萨布素将军传》两部说部,分别讲述了清代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成长经历,他出任黑龙江将军后率部开发和治理黑龙江的业绩,率领北方各民族将士进行抗俄斗争的历史,歌颂了八旗将士和边疆各族人民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上述说部,部部雄浑悲壮,几乎都带有史诗的性质。另据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先生介绍,在《乌布西奔妈妈》《东海窝集部传》《东海沉冤录》《萨大人传》等满族说部中,传留有许多关于开拓黑龙江北广阔寒域,库页岛上的土民与其生活,鄂霍茨克海沿岸的古代村落、渔猎生产,乌苏里江各支流的开发,锡霍特阿林窝集部落,东海的开发与探海,征海岛野民的历史资料,特别是精奇里江各支流的开发、鹰猎、晚期的农耕状况以及“江东六十四屯”历史沧桑的历史资料。同时,说部对于明朝与女真的交往,马市的内幕,王杲与王兀堂等的反明,扈伦四部之争锋角逐,东海窝集部与乌国的关系,努尔哈赤创建八旗与对女真诸部的分化、流徙、恩威手段,对萨满和各堂子的焚戮,等等,都有反映,对各部族祖先亲身受利或蒙难的细情作了叙述。此外,在满族说部中,对于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沿袭很久,现已无复存在的生产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等也都有十分翔实和细腻的叙述,如《红罗女》中的北方古悬棺习俗,《东海沉冤录》中在喜鹊巢中藏男女定情信物的鹊媒风习,《尼山萨传》等说部中萨满教昏迷术的原始形态和心理机制、萨满神判的习惯法、原始符号与原始声动信息的社会意义等,还有北方民族诸如雪屋、雪浴、雪中育婴、医病按摩、古代歌舞、工艺、窖藏、酿造以及天文地理、动植物种类等丰富的知识与技艺等等。这些今天已不复存在的生产、生活习俗与精神文化创造,对于我国北方诸民族的人文研究,都是极为难得的珍贵资料线索。

三、满族说部的传承与衍化
满族说部在传承与播衍方面具有封闭与单一的特点。满族说部产生与流传的历史虽然久远,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满族说部仅凭口耳相传,且只在氏族内传承,族群内部能够讲唱说部者仅为少数长者或萨满。满族各部族众将说部内容视为祖先遗事,没有向族外与社会传播的意识,致使许多说部珍品仅流传于一些姓氏望族的口耳之间,极少形成书卷或手抄文本。正如《爱辉十里长江俗记》所载:“乌勒奔己事,不言外姓哈喇闻趣话。盖因祭规如此。凡所唱叙情节,与神案谱谍同样至尊,享俎奠,春秋列人阖族祭仪中。讲者各姓不一,有穆昆达,有萨玛。而萨玛唱讲者居多,睿智金口,滔滔如注,庶众弗及也。”在满族民众眼中,“乌勒本”即是本族的族规祖训,氏族成员,不分首领、族众或男女老幼,常在隆重的祭礼、寿诞、庆功、庆丰收、婚嫁、氏族会盟等家族圣节中,分等序长幼围坐,洗耳聆听。讲唱说部,一般多是在晚上或白天某个固定的时间,往往连续讲上十余天,多则数十日。有时适逢族群有群体性活动,如到外地征战、田狩或往至营地农牧等,也常请色夫前往进行节选式讲唱。北方冬长夏短,冬日雪天庄稼上仓后,村寨喜听说部。这种古习一直沿续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基于这一民族传统,历史上,满族各氏族部落在选定酋长、族长、萨满时,条件之一便是要求当选人必须有一张“金子一样的嘴”,也即必须具有讲古的才能,如此才能入选。同时,入选者还担负着遴选讲唱说部的后代传承人的任务,并负责对其进行传承与指导。
说部的文本一般都是以一个主要的故事情节为主线,以此为轴,辅以数个或数十个枝节故事链烘托,环环紧扣,纠结成错综复杂的矛盾整体,进而形成宏阔的长篇巨部,如此繁复的讲唱内容自然很难全凭记忆和口耳相传,也需要一定的助记手段。最早的助记手段一般是刻镂、堆石、结绳、积木等方法。据富育光介绍,他所了解的满族说部老一辈传承人的助记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例如: 张石头在布条上做符号助记,杨青山用铁条在木板上烫出符号,白蒙古用石头在土墙上掏洞,还有用皮块、皮条助记的。到了富育光的父亲富希陆先生那里,因满族已开始使用汉字,身为文化人的富希陆先生有一手好书法,他是用毛笔在卡片上写字记忆的。同时,满族一些姓氏与名门望族为了沿袭念祖、颂祖的传统,还纷纷利用谱牒、神本子将本氏族族史及祖先的英雄业绩予以记载、保存并代代传述。
在满族说部系列中,有一些性质比较特殊、严禁外传的“祖宗秘史”。这类说部的传承自然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严禁写成文字,只许口耳相传,心领神会,唯恐外泄流失,造成对祖先的不敬及给族人惹来麻烦。据吉林呼伦纳兰氏秘传说部《扈伦传奇》的传承人赵东升介绍,其家族纳喇氏赵姓是个具有六七百年历史、传承近三十代的名门望族,祖上经历了数次兴衰与沧桑巨变的时代转折,曾传下大量的逸闻和秘史。后金天命末年,纳喇氏赵姓满族的直系祖先洪匡,曾率乌拉部起兵反抗努尔哈赤,后被抄家灭族。“洪匡事件”虽未对后金政权构成威胁,却为清王朝长期忌讳,禁止传播。为隐瞒历史真相,清代诸书均未对此有所记载。清初,乌拉部得以重振,获准祭祖茔、立堂子、续宗谱,纳喇氏的达尔汉等人在纂修家谱时,将满文《洪匡失国》的题名如实地录入了洪匡一系,但对《洪匡失国》的内容只字未记。然而,“洪匡失国”毕竟是清初发生在纳喇氏家族中最重要的事件,祖先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世族人自然难以忘怀。此后二百多年间,族人对此事的仇恨之心有增无减。为使子孙后代永不遗忘,传下了《洪匡失国》这一说部故事,同《扈伦传奇》中的传说并列,作为纳喇氏的秘史。因涉及祖先秘史,家族始终处于高度警惕和保密的状态,祖先规定此说部严禁外传,族内要代代延续,不准失传。一般在烧香办谱时由穆昆达或大萨满在神堂传讲,为时一到三天,平时不准讲述。除此之外,每当过年除夕夜,家长可以在祖宗案前对家庭成员、儿女子孙传讲,听者不准对外透漏,也不准提问。赵东升祖父的《洪匡失国》说部文本产生在清亡之后,在清代根本不允许用文字记述。赵东升曾调查过所有的纳喇氏赵姓后裔,没有一家拥有《洪匡失国》说部的文本,皆为口传,一些支系甚至连口传都没有延续下来,仅保留有对“洪匡失国”这一词语的记忆,对具体内容全然不晓。可以说,像《洪匡失国》《扈伦传奇》这类说部,是满族一些氏族冒着极大风险才传承下来的。

据一些年长的说部传承人介绍,乌勒本并不似现在我们见到的说部那样繁复冗长,动辄几十万字,乌勒本字数较少,基本上是“骨架”,一般都是梗概。无独有偶,笔者近年来在对辽沈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的调查中也发现类似状况。1924 年生人的何钧佑老人,其家族世代传承多部反映锡伯族先民部落时期生活与英雄业绩的传奇故事,经笔者指导采录整理的一部《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便有二十多万字。何钧佑老人回忆,其祖父当年讲述《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时,曾在同村一韩姓族人家中见到用锡伯族文字记载的书稿,是记在一个黄布折子上的,内容比较简单,仅是梗概而已,由此或可印证乌勒本的原始状貌。
与其他类口头文学一样,满族说部在传承过程中自然会发生变异。随着时代的前进,氏的繁荣,满族共同体内不断分化出各个支系,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的说部传承人,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不同支系的传承人对说部内容的理解和认识有别,在说部传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对内容有所加工、调整、升华。尤其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已经深广,满族乌勒本这一古老的民问说唱艺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发生了较大的演变。其时,乌勒本的传承人已渐由满族各氏族中热衷于讲古传统的文化人为主角。此中的一些人由于在朝廷为官,有接触文书档案和文献史料的便利,同时受汉族评书艺术的影响,主动对前人传下来的乌勒本进行补缀勾连,使原本内容比较单一、形式比较简单的乌勒本,经不断的艺术加工,逐渐衍化为首尾相接、情节曲折、内容丰富的长篇传奇巨制,也即成型为今天所指称的“满族说部”。
这一时期,也是满族各氏族讲唱说部活动最为活跃的阶段。除前述带有“祖宗秘史”性质的说部仍保持秘密传承之外,在此期间,满族各氏族之间已经时常举行讲古比赛,甚而搭棚竞歌。清人撰写的民俗笔记《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记载:“满洲众姓唱诵祖德至诚,有竞歌于野者,有设棚聚友者。此风据传康熙间来自宁古塔,戍居爱辉沿成一景焉。”当然,这种讲唱活动与汉族的评书表演仍有本质的不同。满族说部不同于汉族的评书表演,任谁随时随地都可以开讲,内容可以广涉武侠、言情、历史演义,满族说部是在乌勒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始终限定为讲述本民族、本氏族、本家族的故事,且沿袭家族传承,恪守讲根子、讲祖先的历史,讲本民族或本氏族的英雄人物的传统,强调忠实于历史,即使对祖先的评价,也要直言不讳,功过是非要如实评述,以警后人。例如,在《扈伦传奇》说部中,“扈伦四部”是明末女真内部争斗中的失败者,为汲取历史教训,该说部便保留有对同宗哈达的批评,在涉及本族直系祖先乌拉王室的种种劣迹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此外,与汉族评书的区别还体现在讲述动力不同上。汉族说评书是有偿性表演,而在说部传承中,讲唱者没有任何酬报,其讲唱的激情全然来自对氏族祖先和英雄人物的崇仰。讲唱说部时,讲唱者一般多喜用蛇、鸟、鱼、狍等动物的皮蒙制的满族传统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有的以说为主,有的说唱结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讲唱者间或伴有模拟动作表演,更增加了讲唱的浓烈气氛。情绪高扬时,听众往往跟着呼应,并击双膝伴唱,场面热烈而凝重。据《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记载:“近世,爱辉富察唱讲萨公布素,习染诸姓。富察家族家祭收尾三天,祭院祭天,中夜后起讲,焚香,诚为敬怀将军之义耳。”这些记载表明,在清代,满族说部活动已经与萨满家祭糅合为一体,有些说部内容,已打破氏族的藩篱,渐成满民族共有的艺术财富。

满族说部是满族历史的“活化石”和满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内容的建构与播衍蕴含着丰富的族群历史及文化变迁的信息。对满族说部叙事进行文化透视及深层剖析,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复原和再现满族文化自然积累、发展的原生形态,引导现代人另辟蹊径进入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洞悉满族社会发展及族群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
原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注释已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