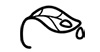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文元
作者:陈文元  创建时间:
2023.03.20 17:05:00
创建时间:
2023.03.20 17:05:00
【摘要】传统农作技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依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其农耕文明悠久,在土地利用技术方面尤为突出。几千年来,布依族于复杂山地环境与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营造了良好的空间结构,实现了人地和谐。基于历史视角,系统审视布依族传统农作技术中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现其在土质区分、种植方法、耕作方式层面有着高超的技术,蕴含着调节生态秩序、平衡生态关系、拓展生态空间、规范生态伦理等方面的生态智慧。合理利用土地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布依族土地利用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地方经验”与“传统智慧”。
【关键词】生态文明;传统农作技术;土地利用;布依族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传统农作技术日益被“遗弃”,但这些技术却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中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生态制度并不过时,对于现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布依族种植水稻历史悠久,稻作农耕是其重要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中国稻作农耕文明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布依族农业生产模式与耕种技术历经几千年的传承,土地利用技术方面十分突出,蕴含着诸多生态智慧与生态经验。
面对复杂的地理形态、多变的气候、有限的土地资源等不佳的农业生产条件,布依族不仅成为开发南方的重要建设者之一,而且还发展了农耕文明。在长久的历史岁月中,布依族基于复杂的地理环境与多样的气候,不断调整和改善农业生产模式与耕作技术,与土地、水、森林、动植物的交互中形成了深刻的生态认知,构建了良好的空间结构,促进了人与自然的深度和谐共生,营造了互惠互利的生态空间。本文基于历史的维度,系统考察其传统农作技术中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方法,分析其中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生态制度,总结提炼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智慧,以期为当前民族地区山地环境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一、农耕文明与地域生态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山川连绵,地形崎岖,但布依族很早以前就从事农耕,以种植稻谷为主,稻作文化在布依族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①。《黔南识略》载:“贵阳则青仲也,善治田。”②民间口传叙事生动记载了布依族的族群历史与稻作文化。例如,布依族神话故事《茫耶寻谷种》讲述的是远古时期布依族先人茫耶与狗不畏艰难获取谷种的过程③。布依族摩经《赎谷魂》中有提到远古时期由鸟儿带来谷种④。布依族古歌《安王与祖王》显示,祖先“盘果王”开创了水稻栽培技术⑤。而《造万物歌》中又提到英雄祖先翁杰传授了如何造田造地,后人艰辛开辟的历史过程⑥。从民间叙事内容看,布依族的农耕文明映衬着浓厚的英雄史诗,这种“人”与“事件”的紧密结合,更加昭示了布依族传统农业耕作与技术传承是远古祖先与自然界共处的交互积累,这一过程可能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
约先秦以前,布依族先民就来到南、北盘江流域生活。那时南、北盘江流域还是荆棘丛生、野兽成群,地形崎岖,环境恶劣,并不适宜从事农耕。即便如此,布依族人依然克服了种种困难,选择靠近河流的地方定居,在秉持敬畏自然的前提下,将不利于农耕的地理环境适度微调,同时又适当改变自身,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了农耕文明。在与自然长而久之的互动中,布依族形成了对山川、土地、河流、森林的深刻认知,根据南、北盘江区域的地理、气候、地形,发展出高超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承农耕文明。
二、传统农业耕作与土地利用
布依族对土地有着深刻理解与认知,主要从土质区分、种植方法、耕作方式三个层面合理利用土地,顺应自然,适当微调,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缓解人地矛盾,实现农作物的增产、增收。
(一)土质区分
南、北盘江流域地质环境复杂,土质类型多样。布依族按照土质属性相应种植农作物,依存有限耕地,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空间。《民国都匀县志稿》在记载地区农业时,对所在区域的土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划分:小土红沙、红油沙、崖粪泥比较耐旱,是比较好的土质,种植出来的稻谷穗大,而大眼泥、鸭矢泥、白油沙、火石土辅之肥力,情况稍好;大黄泥、白善泥、豆麪泥、蕨巴泥则不然,即便肥力得时,无奈过于贫瘠,种植的农作物收益不大,冷白沙、冷黑沙亦同。有些土地虽然比较肥沃,但不同的土地适宜的农作物不同,譬如漕沙泥、黑汕沙,适宜种植菽、稷,但不能种植稻谷,是为山坡上地。在区分土质时,又称“惰农能美者使恶,良农能瘠者使肥,是视人为之”⑦,强调土质只是客观因素,主要在于人的努力与勤奋,体现出布依族朴素的农业生产哲学。
如果土质较差,还可通过人工积肥来改善土壤质地结构,增强农田与耕地的肥力。布依族在长久的农业耕作中,积累起一套蓄肥手段和方法,顺应自然的同时,又能根据自然界的不同资源适时改造自然。依《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所记,传统时期布依族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积肥:一是圈粪,以牲畜粪便为肥;二是收集人的大小便;三是草木灰,乃柴草的灰烬;四是拾牲畜粪便为肥,还有秧青肥、肥泥等⑧。积肥使原本贫瘠的土地获得了肥力,优化了土壤结构,不仅适宜种植农作物,更扩大了耕种面积。不同土质之间,积肥成为一个“中转媒介”,缩小了土质差异。传统时期的积肥方式多采用动植物原料,具有循环再生性,对环境污染小,生态危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种植方法
布依族将有限的土地进行规划分类,调配不同土地的使用方式,巧妙安排农作物种植区域,以优化耕地空间结构,扩大种植面积。例如,将耕种土地分为旱地、水田、轮歇地三类,按需种植,因地制宜。再如,山间平坝或河谷开垦农田种植水稻;荆棘丛生的山坡上种植包谷、小麦、豆类、薯类等旱地作物;沟涧或山间旱地种植甘蔗、油桐、蓝靛、茶树和蓖麻等经济作物。间段种植的是轮歇地,或者是第一年先种包谷,第二年接着种旱稻,然后抛荒轮歇。当然,轮歇并不代表长期荒废。一些较陡的坡地,种植数年后,因水土流失或土地肥力已尽,不能再行种植,继而抛荒,待放至10年后,地力恢复,又可开荒耕作了⑨。
《民国独山县志》对境内的土地类型与农作物种植进行了记载:“不驻祇宜种杂粮,要各所宜。沙地宜棉,坞地宜桑,高亢之地宜小米,高寒之地宜麦与高粱,地处荒僻且多硗。”⑩民间歌谣称,“开田种谷子,开地种包谷,坡头好种棉”⑪,指水田种稻谷,旱地种玉米,坡头种棉花。《种棉歌》中讲,先用勾镰掉刺蓬,然后放火烧成灰,“又用亮亮的条锄去挖,把泥块耙得又碎又细”⑫。至于蓝靛,是利用山间坡岭地散种,诚如《栽靛歌》所说“坡坡岭岭,山山坳坳”⑬的广泛山间地带。
开垦出的农田分出多种门类,便于经营管理。例如坝上田和山岭田,坝上田是河谷山间坝区开垦的水田,山岭田即梯田。再如炕冬田与泡冬田,炕冬田秋收后不翻犁,泡冬田是指秋收后翻犁并放水泡田;还有塘田与干田,塘田指秋收后需加高田埂,抬高水位以便进行稻田养鱼的水田,干田是指放干水源另做他用的田;向阳田与背阴田则是以田指向阳/背阳为区分,一般指梯田。即便是相同类型的农田,基于功能属性,还可更细致地区分,正如“上方拿来做秧田;带到下方撒,下方拿来做母田”⑭。
布依族喜种植旱稻和折刀糯米,施耕于烂田和冰水田。烂泥田不适用挞斗,但恰巧这类糯谷又适宜在烂泥田里种植。折刀糯米是指收割时一刀一穗地折下,将稻禾捆扎挂起晾晒,待至其晾干时,再用棒捶击打脱粒,用石磨碾成白米,可制作成各式美食。旱稻的特点是耐旱耐寒。种植旱稻之前,先烧山,大量草木灰屑留存在土地上,形成了富含碳酸钾之类的肥料,然后下种耕作。不过,旱稻产量并不高,其优势在于可以种植在一些缓坡上,坡度30°左右的山坡皆能种植,不占用平地农田。
耕作过程中,根据土地类型与农作物习性,实行轮种、套种、混种、间种、交叉等多种方法结合。例如,开荒当年先种棉花,第二年种小米、马耳艾,第三四年种包谷,依据土地情况每年种植不同的作物,实行轮种;再如,包谷分粘包谷、糯包谷和黑包谷三种,实行交叉混种;在种植棉花、包谷的土地或菜园内,间种棉花、豆类、芝麻及蔬菜等⑮。布依族古歌《姚平介与囊荷斑》记载了棉、芥间混套作:“谁在山野采苦菜?谁在棉花地里采芥菜?”⑯
《石头寨里好后生》记载了荞、稻轮种:“三四月,荞花堆白银,七八月,谷子铺金毡。”⑰布依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样的种植方式,以更加合理化的方式使用山林土地。
(三)耕作方式
囿于篇幅,笔者无意将布依族传统耕作方式一一介绍,只是基于布依族对土地的开发与利用选取其传统农作技术中一些比较有地域特色的耕作方式,如刀耕火种、梯田、“稻鱼鸭”等。
1.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又名“刀耕火耨”“火耨刀耕”,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一种古老的耕作方式。明代贵州按察司副使阴子淑诗文载:“烧山夷僚隔溪西。”⑱布依族民歌唱道:“过了一山又一山,抬头不见火烧山。……过了一坡又一坡,抬头不见火烧坡。”⑲布依族《铜鼓十二则(调)》里则有“二月清理寨上来烧灰,火苗向外飘过去,火苗向内跳起来”⑳的描述。前引《种棉歌》中也有放火烧刺蓬㉑的记载。这均表明传统时期刀耕火种是布依族重要的耕作方式。
传统的刀耕火种并不会造成森林覆盖减少,更不宜简单地将刀耕火种视为一种落后的、低级的耕作方式。刀耕火种是南方少数民族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基于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与自然、社会,乃至人类生境结构的适应与协调。“如果从农业形态的角度看,刀耕火种可称之为森林旱作轮歇农业。”㉒而且,考虑到西南山区的地域环境与历史因素,刀耕火种很可能不仅不会造成水土流失,产量也并不低㉓。刀耕火种是珍贵的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㉔。应充分挖掘刀耕火种农业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生态智慧,服务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2.梯田开发
勤劳智慧的布依族在极为不利的自然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农业生产,很久以前就在云贵高原的河谷、平坝、山丘之间开辟了大量的梯田。神话叙事歌《查白》中有这样的描述:“古老的年代,记不清时间,黑羊大菁最西边,有座依姑山。古老的依姑山,九坳十八弯,坳坳好坡地啊,弯弯好庄田。”㉕布依族古歌《造千种万物》也说:“翁戛老祖先,怎样来开田?”古老的年代,布依族先辈生活的地方到处还是荒坡,山川连绵,翁戛“搬石头,砌成石坎坎”,然后“用衣兜撮泥,造成块块田”㉖。翁戛在荒坡“搬石、砌坎、撮泥”造田,是对梯田建造的形象描绘。布依族摩经《赎谷魂》中有“好粮选种高弄田,谷粒抛上天,谷粒撒四面”㉗的语句,其中“高弄田”是地势较高且向阳的田,所指正是梯田。《民国都匀县志稿》载“坡陀斜下则为梯田”㉘,提到的即是都匀县的梯田。
作为景观,梯田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布依族对大地的雕刻和艺术加工。但实际上,梯田的核心要素是要解决山区有限土地资源的农业耕作问题,缓和人地矛盾。布依族生活的区域山川林立,沟涧纵横,平地极少,要在这样的复杂地形开垦农田,种植农作物,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布依族在与自然界的互动中,透视山川、河流、森林的关系,顺势利用又适时改造,以高超的经验智慧开发了层层梯田,拓展了土地空间,成为解决山地环境耕地稀少与稻作农耕协调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梯田开发是现实地理形态、耕地资源有限、人口滋生的不利条件下的重要土地利用策略,是布依族因地制宜地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体现。
3.稻鱼鸭
“稻鱼鸭”是布依族农业耕作中的又一大特色。布依族稻田养鱼的历史或可追溯至远古骆田农业时期。布依族神话叙事歌《查白》中提道:“开个池塘好喂鱼,留块荒地好喂马。”㉙布依族《敬酒歌》中讲道:“忙去园中挖姜蒜,又去田中把鱼捉,”㉚还有“水在高岩石下流,鱼在田中水面游”㉛,都是描述田中养鱼的情况。至于在稻田中养鸭,布依族摩经《驱虫记》中有“鸭子下田把虫捉,公鸡坎上捉虫忙”㉜的内容,可视为是田中养鸭的描写。《民国瓮安县志》曾有某次气候异常,狂风“将田中鸭子冲高数仞”的描述㉝,均是对布依族“稻鱼鸭”耕作方式的明确记载。
稻田养鱼可视为一种“立体式”的套种,将农作物种植与动物养殖有机结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行这一生产模式,是布依族视有限水土资源情况下的趋利避害,顺应自然、适时改造利用的聪明智慧体现。作为稻田养鱼文化的延伸,布依族还在稻田中养鸭,同一块田中既养鱼又养鸭,形成“稻鱼鸭”的生态农业。秧苗、鱼都是鸭的食物,鱼也会吞食秧苗,在稻田中养鱼、养鸭看似不太可行,但只要掌握时间规律即可顺利放养。稻田养鱼、养鸭一般在栽秧之后,将雏鸭赶入田中,早放晚收。田间设置深水区的“鱼屋”,且放养的鱼已稍长成,鸭同样无法吃到鱼。秧苗在稻穗未成熟前,鱼、鸭一般不会吞食。而稻田中的虫子、杂草、浮萍,却是鱼、鸭最好的食物。
同时,鱼、鸭的排泻物肥沃了农田,改善了农田的土质,鱼、鸭以虫为食,有效减少了稻田虫害机率。另外,鱼、鸭在田间穿梭,撞动秧苗,增加水稻授粉机率,可实现稻谷增产。待至稻谷抽穗,鱼、鸭已长成,先收肥鱼,再将鸭圈养收蛋,然后收割稻谷,真可谓一举多得。
三、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智慧
传统农作技术表现出文化与经验的适应,“民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其实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配置”,这样一种配置是“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建构起来的社会规则和生存方式”㉞,对于现代化农业发展依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虽然土地资源有限,农耕条件不佳,但布依族却在有限的耕地上种植了多种农作物,以不同方式拓展土地空间,体现了布依族高超的空间意识。“生态环境蜕变的原因并不单是利用过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利用方式上的失误。”㉟布依族对土地的分类和耕种方式选择使土地利用与生态结构达到契合,是重要的“地方性知识”和农业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
(一)调节生态秩序
传统农作技术中的土地利用显示出布依族农事结构的合理安排与巧妙设计。对山林土地的空间使用,是在尊重自然、循环耕作、因地制宜的前提下进行的,土地与农作物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空间布局与文化秩序,蕴含着深厚的生态哲理。
根据土壤质地,布依族人对土壤进行分类,然后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不同土壤“要各所宜”。种植区域上,水田、旱地、轮歇地相结合;在有限的土地资源里,根据土质情况和空间分布,合理利用坡地、山地、沟涧、水田、旱地、林地,建造梯田,人工积肥,改善土质,又辅之轮种、套种、混种、间种、交叉种植等。
开发利用土地,但并不破坏生态秩序。为保证稻田的水资源需求,布依族往往只会将所在地区10%左右的土地开发出来作为农业耕种用地,其余的用做水资源涵养或林木生长之地。开垦梯田严格遵守森林、农田分界线,比如农田与农田之间有灌木、杂草的田埂,农田与森林设置隔草带,在梯田分界线之上保留森林涵养水源,只在山坡的缓坡面开发梯田、旱地,而陡峭面保留原有植被,形成较为分明的耕地—森林平衡的生态秩序。
生态环境可视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内,生物种群皆有各自的位置,即“生态位”,是一个生物在物种与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并随着生态的演替循环发展㊱。根据生态位原理,通过一定的人为调整与约束,保护生物的生态系统位置,使不同的生物在其相应的生态位上,既能使各种生物竞争互克,又能相安而居。以布依族为代表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劳作没有破坏土地、山川、水、森林的生态位,更不是对生态的掠夺,“而是一种通过开发和补偿两种机制实现自调适的文化系统”㊲。系统审视布依族整个土地开发与利用过程,井然有序,事事有依,其以土质、土地空间结构和农作物属性调配种植节奏与种植区位,适时微观协调,建立起一套循环、完善且具有生态保护意义的农业耕作秩序。
(二)平衡生态关系
布依族的土地分类与农作物布局,是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然地理环境发展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既能最大化利于农作物产出,又能合理使用土地,在土地与农作物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空间布局与生态关系。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并不适宜开展大规模平地农业生产,必须根据有限的土地资源合理划分种植农作物。布依族将耕种的土地分为旱地、水田、轮歇地三类。旱地主要种植包谷、豆类、高粱、红薯等比较耐旱的农作物;水田种植水稻、油菜、甘蔗等;轮歇地则作为水田与旱地之间的一个平衡与调节,当水田与旱地空间不够或者地力需要恢复时,适当转移到轮歇地耕种,缓解土地资源紧张,使地力恢复。
长期在同一处土地上连续耕作某一种农作物会出现“连作障碍”,造成农作物产量减少、品种低劣,所耕种的土壤由于消耗过度,地力消失,致使农作物病原微生物滋生,引发土壤结构失衡㊳。布依族传统的多样化种植,不仅能够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还能改善土壤结构,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譬如,稻田里适时种植豆类,可以增加土壤的氮元素成分,增进土壤肥力;麦类农作物根系发达,种植小麦可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油菜根系可分泌有机酸,种植油菜能够溶解土壤中的难溶性磷素,等等。
山区土地稀缺,但人口却不断增加,因而维持现有耕地就显得十分重要。布依族重视土地维护,每年挖地“过冬”,开春后修整田间地角,防止水土流失,对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的地方进行修砌。在布依族的生态观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和谐的、互惠的。维护自然生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人的作用不可替代。在适应自然、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布依族通过一定的人为措施来适时改造自然,通过人的作用来调节生态平衡。
(三)拓展生态空间
充分利用土地的同时又不破坏自然环境以获得绵延长续的生存空间,是布依族世代思考并不断实践的目标。具体而言,一是基于土质不同,合理安排谷类、豆类、蔬菜类、瓜类、竹类、木类、卉类、果类等的种植,规划有限地理空间。区分土质,合理划分种植农作物至关重要。二是通过施肥改善土质。土质参差不齐,可以通过人力为之。肥料成为不同土质间的“媒介”,缩小了土地差异,扩大了种植面积。三是将土地分为旱地、水田、轮歇地三类,采用轮种、套种、混种、间种、交叉等多种方法,改进耕作技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四是顺应山地环境,以刀耕火种适度开辟山林增加耕种土地,发明“稻鱼鸭”立体农业模式,营造特色空间生产。
梯田开发是布依族拓展土地空间的重要代表。其极大地拓展了农业生产空间,解决了人口滋生与耕地有限而造成的人地矛盾。不仅如此,大量梯田涵养了水源,层层梯田,相互环套,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构建了山地一体的育水、增水、保水的农田生态系统。梯田中的土壤、农作物、水、微生物,以及气温、气候、森林、山地等构成了整体的生态系统,农田、作物、动植物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克制。
(四)规范生态伦理
在布依族传统生态观念里,强调“自然是主,人是客”,如待之不敬,便会招致灾难,认为土地、山川、树木、河流、石头、动植物皆有灵性,体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更凸显出朴素的伦理意识。布依族农业耕作过程中对自然、天地、鬼神的认识,往往通过一些传统的宗教仪式、民俗事象表达出来。这些农事文化表达,也可以归类为一种“农作技术”,其目的或是祈求农作物免遭虫害,或是求神降雨灭灾,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定的生态哲理。
例如,在滇黔交界威宁地区的布依族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十五这几天,聚集在红岩大山过“蚂螂节”。蚂螂即蝗虫,是稻田虫害,民间用稻草扎成球状用来驱赶蚂螂,保住庄稼。又如,农历二月初二“破土节”,布依族会祭祀“土地神”和“灶神”。农历六月初六则有“祭水口”“祭山神”“祭山地”等活动。此外,还有“迎春雷”“开秧门”“祭青蛙”“地蚕会”“扫坝”等。这些农事文化映衬了布依族对农业耕种与收成的愿景和希望,将人与天、地、人、动植物、森林、水的关系确立起来,对人们日常一些“越界”“失范”行为进行矫正、警醒,甚至惩戒,无形中强化了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
敬畏之心下,布依族有着维护生态、爱护自然的社会责任,土地、山川、树木、河流、动植物都是受到保护的对象。一方面,通过一些乡规民约、日常禁忌、行为规范,乃至建立惩罚机制,限制人们的一些不合理活动,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秉持适度原则,不过多地向大自然索取,适当休息,给予大自然自我修复的空间和时间,缓和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布依族的农事文化,无形中规范了布依族的土地开发与利用。
结 语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的农业形态与耕作方式因历史上“落后”“低下”的标签而不受重视。如果仅从生产力与生产量来看,它或许是如此。但所谓的“先进”,是相对“人”而言,还是“自然”而言呢?从现今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的结果来看,显然是前者。但人类从来都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者,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而不是从自然界的整体格局出发,必然会造成自然界系统的失衡。从这个层面来讲,布依族传统农耕与农作技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是有价值的。作为南方少数民族中稻作民族的重要代表,布依族发展了高超的农耕技术,构建了适宜的人与土地、人与动植物、人与水、人与森林等的关系,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极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并使之转换成现代文明,提升为现代的生态伦理观㊴。从布依族传统农作技术中吸取有益的生态经验与生态智慧,或是一条可行的实践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认知人类学视域下西南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研究”(项目编号:18XMZ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文元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历史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