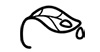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宣炳善
作者:宣炳善  创建时间:
2023.10.08 14:58:00
创建时间:
2023.10.08 14:58:00
民俗学在20世纪初由周作人等学者介绍到中国以来,通过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黄石、刘魁立、乌丙安、刘守华、刘铁梁、陈勤建等现当代民俗学家的不懈努力,已取得不少成绩。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全国征集的歌谣选。自此,钟敬文指出,中国现代性质的民俗学学科发端于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①。中国民俗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科探索与发展,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格局已经明晰,并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这三种研究范式分别是民俗文化学研究范式、民俗主体学研究范式、民俗生活学研究范式。三种研究范式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三大流派,三大流派三足鼎立,并互为影响,从而呈现出民俗学学科的内部丰富性与内在张力。在民俗学的三大研究范式中,陈华文的民俗学理论研究独树一帜。2014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华文所著《民俗文化学》一书,将“独特生活方式”的概念引入民俗文化学研究,破除了民俗学界长期以来盛行的民俗既是生活又是文化的双重结构说,并将民俗文化学研究范式与民俗生活学研究范式有机结合,因此需要在学理层面进行相应评价。
一、三大民俗学研究范式的理论探索
(一)民俗文化学研究范式
民俗文化学的研究路径是将民俗作为文化传统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范式侧重的是民俗的“俗”,即民俗的文化属性。民俗文化学经由钟敬文倡导,已成为中国民俗学的学科主导范式,大量的民俗研究集中讨论的是风俗这一文化文本本身或民间文学这一文学文本本身及其历史变化。钟敬文在《“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民俗文化”这一概念②。1991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民俗文化学发凡》的学术讲演,强调中国民俗研究与中国文化结合,将民俗作为文化的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钟敬文所著《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一书,开展系统讨论。这一研究模式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民俗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即民俗事象一般具有历史遗留物的特征,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认知。这是通过民俗研究的方式进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路径。
陈华文在《民俗文化学》一书中,也指出民俗文化学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俗学,将民俗置于整个文化背景下开展考察,从而使民俗不再成为孤立的事象,而是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去认识,因此,使民俗的价值、作用与意义都得到了重新定位和确认③。
从学术脉络上分析,《民俗文化学》受到了钟敬文倡导的民俗文化学学科的影响,但在具体的学科建设上,作者有自己的理论贡献,其理论贡献首先在于突破了钟敬文提出的三层次文化分层法,即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并将“独特生活方式”的概念引入民俗文化学研究。钟敬文提出的三层次文化分层法是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侧重的是民俗主体的社会身份的差异性,即认为上层文化是地主阶级创造与享用的文化,中层文化是市民创造与享用的文化,而下层文化主要是农民与其他劳动人民创造与享用的文化。钟敬文认为中下层的文化就是民俗文化,而上层文化不是民俗文化。但陈华文认为,三层次文化分层法过于强调三者的相异性,忽略了三层次之间的互动交流,而民俗传承者的身份是在不断变化的,是依社会情境而确定的。陈华文指出,古代的官员,从阶级上说属于上层文化,但其社会身份却随着社会角色的变化而变化,如这位官员在家里,就是儿子的身份,或者父亲、丈夫、祖父等多重身份,而与他人社会交往时,也会呈现不同的社会身份的转换。正如历史上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上层文化的礼仪与民间的习俗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因此陈华文认为,上层文化并不总是由地主阶级创造与享用,而下层文化也并不总是由劳动人民创造和分享。民俗文化的三层次结构分层,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的分隔④。由此可见,陈华文的民俗学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探索更强调情境化的民俗学研究,也就是对生活中的民俗活动的深入研究,即认为民俗文化是所有民众共同享有的文化,而民俗传承者是一个复杂的群体。陈华文对民俗文化全民性的理解,实际上还是从民俗生活论中脱胎而来,民俗生活是全民共有的生活方式,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民俗文化当然也是全民的文化。
(二)民俗主体学研究范式
民俗主体学的研究侧重民俗的“民”的问题,即侧重研究民俗主体问题,即是谁在创造、组织、传承、发展、分享民俗。这一研究路径涉及主体间的伦理问题,而在国家非遗保护的行政语境下,又涉及普通民众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化身份转化的研究。英文“folklore”译成汉语在民俗学界曾有多种方案,江绍原曾译成“民学”,没有译成“民间学”或“民众学”,但后来“民学”的译法并没有被钟敬文与汪馥泉采用⑤。民俗学对“民”的概念思考经历了民间、农民、民众、人民、公民、非遗传承人等不同的学科定位与反思,并逐渐与“公民”这一法律话语与“非遗传承人”这一文化话语相结合。
顾颉刚在1928年的《民俗周刊》发刊词中认为民俗学就是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将民众文化从贵族的圣贤文化中解放出来,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并表明自己就是民众⑥。在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学学科的“民”的系列思考以高丙中的积极探索为代表,高丙中指出民俗的实际表演主体与声称的名义主体存在差别,谁被认定为民俗的主体而被学术之眼盯住,其日常生活就会成为民俗学的调查对象,而吊诡的是民俗学学者与民俗主体的伦理关系,即被研究者作为民俗主体在民俗学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往往沦为否定改造的对象。民俗学者通过这样的研究,提升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但民俗主体的主体性却无法建构。因此,要反思民俗学者的职业伦理问题⑦。实际上,高丙中说的是民俗主体的互为主体性的问题。民俗学学者同样也是民俗主体,与被研究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即互为主体性的问题。陈泳超对于民间的知识分子使用了“民俗精英”的概念,并界定为仅限于在特定民俗事项中发挥支配性作用的人,如老支书于占辉,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他在接姑姑迎娘娘仪式活动中是重要的当事人⑧。民俗学学者善于书写,而民间意义上的“民俗精英”也善于书写。民俗学界“民俗精英”概念的提出,对于提升民俗主体的文化主体性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自2004年以来,对非遗传承人本身的民俗主体研究,也是民俗学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在“民”上面,有如此众多的民俗学学科机遇,这确实是钟敬文时代的民俗学学科所无法想象的。同时,这一研究范式还揭示了民俗组织学与民俗伦理学两个分支学科的发展方向。民俗由于是群体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俗活动的开展往往需要形成一定的社会组织,如香会、香社、进香团、谒祖团、观音会等信仰型组织,这就涉及到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如社会合法、行政合法、政治合法、法律合法的社会团体的四种合法性⑨。国内对于民俗组织的研究,多集中在信仰型庙会,其中以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叶涛所著《泰山香社研究》一书与201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岳永逸所著《朝山》一书为代表。叶涛研究的是明清以来的泰山香社,岳永逸研究的是当代妙峰山香会,这两本书研究的都是碧霞元君这一地方神祇。民俗学界自顾颉刚研究妙峰山香会始,通过吴效群等人持续研究妙峰山香会这一民俗组织,已形成了中国民俗学的民俗组织研究的传统。民俗组织也是民俗主体,只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因此,这一研究方向将极大推动中国社团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而民俗伦理学研究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如民俗学者与民众的伦理关系、民众与动植物以及自然界的伦理关系、民众与神灵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研究等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十二条非遗保护的伦理原则的核心是尊重的原则,说的也是主体间的伦理关系。《民俗文化学》一书,在其新修订的第七章中,也讨论了民俗主体问题,即民俗学者对地方民众的民俗文化解释的尊重问题。
(三)民俗生活学研究范式
民俗生活学的研究路径是将民俗置于复杂的生活语境中展开分析,特别是当下的生活语境。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民俗,还是在仪式生活中发现民俗,都是从生活的视角分析民俗,从而考察民俗与生活的复杂关联,并进一步丰富对生活本身的理解。中国民俗学界将“表演”“语境”“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民俗事件”等概念引入学科话语分析时,实际上是把民俗活动当成具体的民俗事件来处理。在这方面,中国民俗学界已取得丰富的成果⑩。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路径主要是面向当下的民俗学研究方式,但是“语境”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当下的日常生活,回到历史现场的历史语境,也是语境使用的一个方法。
《民俗文化学》的学术贡献在于将民俗生活与民俗文化有机结合,但是并不将生活与文化放在同一层面开展分析,而是采用将民俗的生活性置于第一位,民俗的文化性处于第二位的分析思路,从而更为强调民俗文化学研究对生活情境性与地方性、民俗个性的关注。
陈华文对民俗文化学的研究是从成年礼、婚礼、丧礼等人生礼俗的民俗事象入手,地域集中在吴越地区,并将民俗生活论观念贯穿到民俗事象的个案研究中。他通过严谨细致的研究将文身这一成年礼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民俗文化的思路还原为民俗生活,从生活的角度研究文身产生的最早原因。通过将文化还原为生活的方式,陈华文发现成人式文身首先形成于女性群体之中,对女性形成性保护,这是文身的最早原因,而对男性则是通过成人式文身表示性行为的限制。通过综合研究指出,文身最早是发生于原始社会不等辈血缘婚时期的婚姻性关系的符号,而原始的性关系是一种生活需要,它是先于文化的,一直到后来文身才成为氏族标志、图腾崇拜等富有文化意蕴的群体制度。所以文身民俗的发展类似顾颉刚所说的古史的层累,即越发展到后来,其民俗事象越丰富,文身民俗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也就越丰富。对文身民俗的研究,必须考虑到文身民俗本身的演变过程,也只有在演变过程中才能发现其特征。文身民俗也有一个从生活需要向文化样式演变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在演变过程中,原有的生活需要并没有失去,而是一种层累的传承。陈华文在文身研究中贯彻了生活先于文化的民俗生活论观念,所以才发现了隐含在文身中的婚姻性关系的意义,也发现所有的文身形式都源出于成人礼文身这一生活事实。
从民俗生活的角度切入,把握了文身的整个演变过程,最终发现三种形式的文身都与婚姻性关系有关。关于文身民俗的个案研究,可以视为陈华文民俗生活学运用最为成功的一个个案。
二、民俗生活学与民俗文化学研究范式的有机结合
《民俗文化学》一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在对大量的民俗事象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主要以陈华文所著《丧葬史》与《文身》两本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陈华文从人生礼仪的民俗事象的研究逐渐上升为民俗学理论研究的过程。如果说陈华文的《文身》主要是从民俗生活论的角度进行研究,那么《丧葬史》则主要是从民俗文化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即从民俗与文化两个角度对丧俗进行研究。在《民俗文化学》中,更是强调历史文化要与民俗生活相结合,体现出陈华文的民俗生活学的观念。
以丧俗为例,陈华文区分了官方的丧葬礼制与民间丧俗的差异,并着重批评了许多丧葬民俗事象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即以官方的礼制丧仪去比照民间丧俗,然后判定谁具有更大的真实性,谁的历史更悠久。而在得出结论时,总是本末倒置地认为民间丧仪是对礼制丧仪的模仿和抄袭。这种以礼制丧仪为标准的思维方式,使民间丧俗始终处于礼制丧仪的笼罩之下。真正具有丰富生活特征的民间丧俗就这样遁出了一些民俗学者的视野。陈华文通过研究指出民间丧仪比官方丧礼更具有地方适应性与生活适应性,因为民间丧俗的内容完全可以随着丧家的不同生活需要而进行增减删削,并且比官方礼制带有更浓厚的信仰内容。如顾颉刚所列的出殡导子账,除了“诰敕亭”等具有历史原型外,其余几十项都是在出丧过程中因为比附而独创添加的,像高跷、台阁百宝箱、渔樵耕读纯粹是炫耀性的内容。正是这种在生活中不断独创添加比附,使民间丧俗更具地方个性与丰富的生活色彩。在民间丧俗的地方性关注上,陈华文同样体现了其理论上的民俗生活论的影响。所以民间丧俗不仅存在丧礼的礼制渗透现象,更重要的是存在明显的地方特征。可以说,在陈华文的民俗个案研究中,他所提出的民俗生活论具有更为全面的理论分析能力。
民俗学在19世纪的英国产生之后,民俗学理论就一直处于争论、发展和完善之中。英国民俗学是否具有普世性意义,是值得讨论的。民俗学主要是对群体性模式化的代代传承的日常生活方式的研究,而民俗作为模式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与国家的差异,因为每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都是不同的。而且由于民俗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每个现代民族国家都有必要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提出对民俗的界定和理论。从学科理论的建设方面看,民俗学理论的最终完善也迫切需要各个现代民族国家从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国情出发,首先提炼出自身的民俗学理论,然后才是世界意义上的各国民俗学理论的对话与整合,最终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俗学理论。理论民俗学的探讨是陈华文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工作,也是取得成绩最多的领域之一。
早在1984年,陈华文就在《民族文化》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俗生活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初步探讨了民俗的本质是生活的观念⑪。民俗来源于生活,而又在生活中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生活性是民俗的本质。在《民俗研究》1992年第2期上,陈华文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民俗本质——再论民俗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论文。独特生活方式的民俗学核心思想在《民俗文化学》一书中得到了沿续与深化。在1992年的论文中,陈华文主要使用“民俗”的概念,而在《民俗文化学》一书中,陈华文更多使用“民俗文化”的概念,将“民俗”置于“文化”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学术视野更为开阔。由于受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框架的影响,对民俗性质的认识往往也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如有学者主张民俗属于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也有学者主张民俗是沟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这些学者由于套用西方理论模式从而牺牲了民俗本身的特征,而陈华文则撇开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纠缠,直接从民俗本体论入手,采用历史维度的发生学分析法来分析民俗文化的产生,结果发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民俗现象,即民俗文化的产生是有层次的。民俗文化产生的层次性问题一直为国内大多数民俗学家所忽视,而这种民俗发生的层次性差异正是区别民俗的生活性与文化性的关键所在。
在《民俗文化学》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陈华文从发生学角度对民俗文化的发生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民俗文化发生的层次性是指民俗在生成过程中的先后次序和构成问题。陈华文讨论了第一层次民俗文化与第二层次民俗文化产生的先后过程。第一层次民俗文化的发生总是直接与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它表现为物质生产民俗和自身生产民俗,也是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产生首先是为了生存和生活,因此民俗文化的生活性始终是第一性的。在物质生产民俗方面,陈华文以游牧部落、农业部落、渔猎部落为例,指出他们在劳动中形成的习俗,都直接来源于不同的生产方式,而重复沿续先人的生产方式就形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习俗制度,并逐渐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⑫。
在自身生产民俗方面,陈华文以婚姻民俗中的群婚为例,群婚的出现是为了人类种群的繁衍,也是出于人类的动物性本能。群婚这种民俗事象的出现首先是为了生活,它是没有文化参与的。但当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第一层次的民俗文化也会相应地发生民俗文化的变异,这种由于社会的变化从而导致原有民俗文化发生的变化就属于第二层次的民俗文化,而正是第二层次的民俗文化才带有文化的影子,才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民俗的生活是第一性的,而文化则是第二性的,它是民俗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作者在书中指出,如果混淆民俗文化发生的层次性,将直接从生产生活中产生、传承的第一层次的民俗文化内容与派生的第二层次的民俗文化一视同仁,则势必对民俗文化的发生和它的本质认识发生偏差⑬。
民俗在其层累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文化的渐次渗透,但其生活性一直是存在的。这样就对那种认为民俗既是生活又是文化的民俗二重结构说提出了质疑,民俗的二重结构说之所以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就因为它是对民俗的平面化的理解,没有意识到民俗的发生在其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一个立体的层次性问题,也没有意识到民俗的发展是一个层累的过程。陈华文将民俗的生活性界定为民俗的本质属性,并进行系统论证,使民俗由文化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真正从理论上突破了早期英国民俗学认为民俗是文化遗留物的认识水准。
在将民俗文化发生的第一层次界定为生活以后,陈华文发现了民俗文化发生的第二层次的文化性特征。在对于民俗的生活性给予最大关注后,他对于民俗的文化性的关注也随着其民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进行着。陈华文的民俗学理论探索从民俗生活论走向民俗文化论,这其中的学术变迁过程具有其内在的学术逻辑性,也体现了他在民俗学理论上的执着探索。
在《民俗文化学》一书中,作者从五个方面,对民俗文化的独特生活方式论进行了详细分析。
第一个方面,民俗文化的产生是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人们往往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包括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两个层面。这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二个方面,民俗文化在传承时,也是以生活方式进行的。
第三个方面,民俗文化即使在传承中忘却了原初的含义,但仍能保持其独有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的内涵不断变异,但生活方式却一直重复,几乎不变。
第四个方面,民俗文化以群体认同、个体实行,并以强烈的独立性的生活方式展现自身。
第五个方面,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于其是文化意识的积淀,即民俗文化是民俗生活的影子⑭。
这五个方面的论述,作者是从发生、传承与变异、心理认同三个维度展开的。从民俗文化的发生维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往往是生产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讨论生活方式问题时,作者注意到了对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生产方式问题,并从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两方面开展分析。从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变异的维度,作者发现民俗文化随历史变化而变化,其文化形式与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但生活方式却一直不变。从心理认同的维度,作者强调民俗文化的独立系统,而这一独立系统,构成了民俗生活的独立性,也成为区别不同群体生活方式的标志。民俗心理作为集体无意识,是附着于民俗生活的一种心理定式,也是群体认同的文化现象,也就是文化的归属感。
当作者在理论探索方面由民俗生活转向民俗文化时,并没有抛弃以前一直坚持的民俗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学术理念,而是把原有学术理念整合到了民俗文化学体系中去。民俗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从生活走向文化,因此对民俗的探讨也必然要关注文化现象。大多数民俗学者在民俗性质的理论问题上,总是摇摆于生活与文化之间而不自觉,但陈华文的民俗学理论探索则十分明确地显示了从生活走向文化,又将文化还原为生活这一理论轨迹。
在该书中作者还系统探讨了民俗文化圈与民俗文化传播两个专题。作者在民俗文化圈问题上借用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圈概念,讨论了民俗文化圈的形成与民俗文化圈的扩张,在民俗文化传播问题上讨论了民俗文化传播的模式与传播的载体。这在国内民俗学界的理论性著作中也是系统性的理论尝试,这也为后来修订本中的区域民俗的分析作了相应的前期理论探讨。
《民俗文化学》一书,最早于1998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重版时,增加了“民俗文化的解释”“民俗文化的多元一体与区域性”两个章节,分别是书中的第四章与第七章。之所以要增加这两章,也是出于民俗学理论完善与深化的需要,后文还将进一步分析。
三、民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与对象体系
《民俗文化学》全书共十一章,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民俗文化学理论体系与对象体系。在结构上,《民俗文化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该著作的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构建了民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相当于著作的上篇。该著作的第二部分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构建了民俗文化学的对象体系,也就是民俗文化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与内容,相当于著作的下篇。
著作上篇的七章,其内在结构具有层层深入的逻辑递进关系。第一章首先讨论的是“民俗”“民俗文化”等核心概念,并分析了民俗文化的研究方法,重点分析田野作业的方法,这也是民俗文化学最为重要的学科方法,关注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并对行为模式的流动性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厘清概念,确立学科方法的基础上,第二章就入手分析民俗文化本质问题,通过发生学的层次分析,指出民俗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可谓开门见山,直抵堂奥。值得注重的是,在第二章中,作者还特地讨论了民俗文化学的社会学意义,认为民俗文化虽然是来自生活中的经验知识,但也具有科学因素,可以发展成为科学知识。同时,民俗文化也参与了社会秩序建设,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在揭示民俗文化的本质在于独特的生活方式之后,第三章则讨论了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功能,在讨论民俗文化的认同、教化、规范、维系、调控、记录六大社会功能时,对于第一个功能即认同功能进行了重点论述,作者认为民众对自身族群有特别的认同感,并以武义方言“擦桌布挂在桌档上”为例,点明武义人的身份认同与武义方言的民俗文化圈有内在关联⑮。这也为著作第六章讨论民俗文化圈埋下了伏笔。
在论述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功能的基础上,在2014年新修订的著作中,增加了第四章“民俗文化的解释”。为什么要增加这一章节?这体现了作者尊重地方民众的学科认知。因为民俗学者一般研究的是民俗文化本身,却没有将民俗文化的解释也作为民俗文化的整体加以关注,没有将其纳入研究的对象。地方民众对当地民俗文化的解释,往往反映了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与多样性,而这种地方性的解释,需要得到民俗学者应有的关注。第四章突出了对当地人、当事人的文化尊重。作者指出民俗学家必须尊重区域之中的民众对于特定民俗文化的解释,而不是为了满足学者的个人想象,民俗学研究应回归生活的真实而不是异化民间的生活,对民俗文化的解释,也是文化自我确认的过程⑯。
在陈华文的民俗文化学的理论框架中,他突出的是民俗生活的研究范式与民俗文化研究范式的结合,而对民俗主体研究范式较少涉及,但在新修的第四章中,则突破了原有的自我认知,进一步关注民俗主体研究,从而建构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俗文化学理论体系。
通过前四章的论述,作者在后面的三章中,进一步讨论了民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异,并对民俗文化圈与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进行专题分析。第五章讨论“民俗文化的传播范式”,在吸收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作者将民俗的纵向传承也视为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传播现象,并认为传播促成了民俗文化圈的形成,也正是由于传播,最终影响了民俗文化的变异⑰。这样就顺理成章,引出了第六章对民俗文化圈的讨论。
第六章“民俗文化圈理论”,讨论的是民俗文化的区域性问题,即关注民俗文化在其发生过程中,会形成相对稳定的不同文化主题的民俗文化圈,而由于社会的发展,通过民俗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民俗文化圈就会发生变化,或者扩大,或者缩小。因为讨论民俗文化圈问题,就必然要讨论民俗文化的区域性问题,也就是民俗文化的空间问题,于是引出第七章对民俗文化多元一体的区域性的分析。
第七章“民俗文化的多元一体与区域性”更多讨论民俗文化的空间性问题,也就是书中讨论的区域性。在原有的文化圈与文化区理论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作者持续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全球层面的文化交流与碰撞过程中,不同区域的群体的生活方式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的问题。区域民俗问题,实际上也是文化的个性化问题,而在全球化冲击下,文化的个性会受到影响,因此传承地方文化,发展地方经济,已成为当代民俗学者的共同问题。作者对文化个性的坚守,其实是对独特的生活方式论的坚守。
通过七章篇幅的讨论,民俗文化学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就形成了。可以看出,陈华文的民俗文化学理论体系是以独特的生活方式为出发点,进而分析从生产、生活向文化演进的路径。在这一路径产生的过程中,就会逐渐形成民俗文化的区域性等特征,在空间意义上,就是形成相对稳定的不同主题的民俗文化圈,并同时行使民俗文化的认同等多种社会功能。而通过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播,民俗文化也在不断变异。在上篇的七章中,作者对地方民众的文化自我解释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可以看作是作者对民俗主体的尊重与关注,也是对民俗文化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著作下篇共四章,分别是物质民俗文化、社会民俗文化、精神民俗文化、娱乐民俗文化,体现了民俗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民俗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这与国内民俗学理论著作中讨论的民俗分类与研究对象基本相同,也就不再评论。
纵观陈华文的民俗文化学的理论探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从民俗生活到民俗文化的探讨,并且将民俗生活上升到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的理论高度的过程中所留下的思考轨迹。陈华文提出的独特生活方式的民俗文化本质,也将成为当代中国民俗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供后人继续研究讨论。
作者简介:宣炳善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与非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