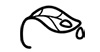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明明
作者:杨明明  创建时间:
2023.10.31 16:39:00
创建时间:
2023.10.31 16:39:00
【摘要】新坪村属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新城子藏族乡辖下,该村藏族民众使用藏语中的安多方言,但不识藏文。在这一背景下,要追溯新坪村藏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文化,口头传统就成为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赤沙龙王传说是糅合了“梦斩泾河龙”的故事与新坪村当地口头传说的产物。作为一则信仰传说,它解释了当地赤沙龙王信仰和新坪村“七月会”的由来以及妇女“骂神”仪式的由来。由于口头传统是存在于民间且不易被社会权力操纵的叙事,因此它暗含了更为隐秘的历史记忆。赤沙龙王传说不仅保存了新坪村藏族的移民记忆,也影射了这一族群在历史上与周边族群发生的种种互动。
【关键词】赤沙龙王传说;新坪村藏族;民间信仰;历史记忆
口头传统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承载了人们的地方观念、审美情趣、生活习惯等诸多信息,具有明显的解释功能。对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口头传统对其历史文化的传承显得尤为重要。在地处藏彝走廊的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生活着一支独特的藏族,由于这一地区在历史上便是众多族群频繁互动的地带,因此,宕昌藏族的族群特征与大众眼中的“典型”藏族颇有不同。2021年7月至2022年8月,笔者在宕昌县新坪村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收集到了较为可观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流传于新坪村的若干口头传说。
新坪村属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新城子藏族乡辖下,藏语名为“ye bod”,意为“居住在上面的藏族”。当地藏族民众认为,祖先是从舟曲迁徙过来的。从地理位置来看,新坪村处于舟曲的上方(北方),因此得名。新坪村目前有212户,常住人口806人①,新坪村藏族民众皆信仰“[luei]”(当地藏语方言读音),即宕昌方言中的“老爷”或“佛爷”,也即龙王神。宕昌县有着和洮岷地区“十八龙神”信仰同属一个体系的“十二龙(灵)王信仰”②,新坪村的藏族民众即信奉位列其中的赤沙龙王。该村藏族民众使用安多方言③,但不识藏文。在这一背景下,要追溯新坪村藏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文化,口头传统就成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广义上的口头传统包括以口头讲述的方式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史诗等口头叙事文学。在本文中,笔者仅以流传于新坪村的赤沙龙王传说作为研究对象,以该传说为切入点来管窥当地的民间信仰并发掘当地藏族的历史记忆。赤沙龙王传说是典型的信仰传说,这一传说在讲述赤沙龙王生平事迹的同时,也解释了赤沙龙王何以成为新坪村的保护神以及新坪村每年举行“七月会”④的缘由。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甘南舟曲的民间传说中,赤沙龙王的原型被描述为北宋名将杨延昭。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过新坪村师家⑤杨红青⑥,从他口中得知,在当地师家口口相传的知识体系中,赤沙龙王的原型为金皇老龙,即《西游记》中的泾河龙王,并非舟曲地区所说的杨延昭。相邻地区同一神祇的来源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这一现象值得做进一步深究。
一、赤沙龙王传说概况
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走访了新坪村的几位师家,在他们的口述中记录了流传于新坪村的赤沙龙王传说。该传说的形态较为稳定,从内容上来看,可拆分为赤沙龙王“被封神前”与“被封神后”,即赤沙龙王的由来和他封神后在宕昌的活动轨迹。
赤沙龙王的由来套用了“梦斩泾河龙”的故事,“梦斩泾河龙”载于今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计拙犯天条”⑦。据学者考证,“梦斩泾河龙”滥觞于民间求雨不灵遂咒杀龙王的巫术心理,泾河龙王减少雨数实际上影射了泾河流域的旱灾,“斩龙王”的传说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渴望征服自然的朴素愿望⑧。
在新坪村的口头传说中,唐太宗被笼统称作“唐王”,泾河龙王被替换为“金皇老龙”(即还未封神的赤沙龙王),袁守诚的姓名被隐去,只保留了他算命先生的标识性身份。原本的减少雨数变成了“将羊毛细雨下作恶风暴雨”,这一改动体现出典型的地域特征。按甘肃省气候分区,新坪村属陇南温带湿润区,历史上很少发生旱灾,反倒因为山高沟深、易降暴雨而存在发生洪涝的隐患。由此可见,在新坪村赤沙龙王传说中,咒杀老龙的目的并非为了祈雨,而是出于稳定降雨量、维护当地生态的需求。在这一传说中,唐王因失信导致老龙被斩,为摆脱其阴魂的搅扰,唐王下令为老龙作法七七四十九天以超度其阴魂,但当时国内的经文不全,遂命唐三藏前往西天取经。将民众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与唐王为赔罪而超度金皇老龙这一传说进行黏合,并使二者呈现出因果关系,这一行为也从侧面反映出新坪村民众有意抬高金皇老龙的地位,使其被超度后受封成为赤沙龙王的这一情节具有了正当性与合理性。
在赤沙龙王传说中,真正蕴含了新坪村藏族集体记忆的是其被封神后在宕昌的一系列活动。据师家口述,宋朝时期,皇帝册封了天下鬼神,派他们前往西部守护庄稼。赤沙龙王被派遣到西金营⑨的高庙山执掌生死簿,因其手段残酷,小鬼们苦不堪言,在玉帝处告了赤沙龙王的御状。玉帝派皇太子(后被封为泰山爷的黄飞虎)接替赤沙龙王的位置,一番争斗后,赤沙龙王败逃至舟曲,在舟曲娶了当地的一位藏族女子作二房,两人在舟曲生活了几年。之后,舟曲一直不下雨,喇嘛们开始驱逐赤沙龙王,双方发生争斗,赤沙龙王又逃回了宕昌。他将正妻金丝娘娘安置在新坪村神庙内,将二房安置在新坪村村口的大柳树下,而他自己在新城子乡的克珠(杈家村,当地藏语方言读音为“[khɔ: tʂu]”)山上又修了一座庙,独自住在那里。因此,赤沙龙王也被当地人称作“克珠阿爷”。每年农历七月,赤沙龙王都会回新坪村和自己的两位妻子团聚。赤沙龙王的二房被当地人称作“阿麽”⑩,因为阿麽是被赤沙龙王强娶,并因此背井离乡,所以对他心有怨恨,每当赤沙龙王回新坪村,阿麽就会附在村中女人的身上,让她们去拦轿痛骂赤沙龙王。
在2022年的新坪村“七月会”中,有三位当地藏族妇女在龙神巡游过程中“发神”⑪,或指着轿中赤沙龙王的神像大骂,或撕扯神像的衣袍,更有甚者,会伸手去拔神像的胡须,上述传说正是解释了这一行为的由来。与师家的交谈中,笔者获悉,早年间,师家还会在龙神巡游过程中,将一枚特制的铁钉穿过左耳,以此象征赤沙龙王的真身降临此地。这一点对应到传说中,乃是皇太子不敌赤沙龙王,突施暗箭射中赤沙龙王左耳,赤沙龙王因此败逃。
由此可见,赤沙龙王传说为“七月会”中的仪式提供了逻辑上的合理性,而这一系列仪式也强化了赤沙龙王传说在民众心中的可信度,传说与仪式相呼应,共同构建了当地民众的信仰空间,从而培育了当地社会文化心理认同方面的一致性。
二、赤沙龙王传说中的民间信仰
在宕昌,龙王神不仅被当作传统意义上的司雨之神,同时也作为地方神保佑一方平安⑫。在这里,龙王神的信仰场域大到供奉着神像的庙宇,小到每户村民的家堂神案。区域性的宗教信仰使单一神灵变得全能化,赤沙龙王的职能范围也因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变得极为宽泛。
在吸纳龙王神进入信仰体系前,宕昌藏族原有的信仰为司巴苯教(即原始苯教)。司巴苯教笃信“万物有灵”,山神信仰是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宕昌藏族普遍信奉凤凰山神,在新坪村,凤凰山神被称为“bya khyung”。山神的神学功能与龙王神相近,皆执掌着自然之力,可护佑一方风调雨顺。这为宕昌藏族接纳龙王神提供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心理基础,而这一点在赤沙龙王传说中即有体现。
在传说中,赤沙龙王被僧侣从舟曲驱逐回来,他赶着几头牦牛,翻过雷古山进入新坪村境内。赤沙龙王面对群山开口,向凤凰山神言明自己的境况,请凤凰山神允许自己在此地落脚。一夜后,在荒野醒来的赤沙龙王发现自己赶来的几头牦牛化作了石头,他明白这是凤凰山神应允了他,于是在石头附近修建了庙宇,并将自己的正妻金丝娘娘接来,落户于此。
在这一情节中,赤沙龙王是在征得凤凰山神的同意后,才得以在新坪村筑庙,由此可见,在赤沙龙王信仰进入新坪村前,当地的原初信仰确为凤凰山神。在走访中,笔者也发现新坪村真正收藏有凤凰山神唐卡的人家只有10户,这10户人家既信赤沙龙王,又信原始苯教。除这10户人家外的其余藏族村民则将赤沙龙王作为主要信仰,凤凰山神只存在于他们的家堂神案之上,相比赤沙龙王,凤凰山神在当地藏族的信仰活动中不具有突出地位。
新坪村藏族的家堂神案分为大案和小案,大案供奉赤沙龙王及其正妻金丝娘娘,小案供奉其子山海龙王与其女金花小姐。金丝娘娘、金花小姐作为赤沙龙王的妻女,也从属于龙王神信仰体系。因为长期与汉族杂居,新坪村藏族以农历代替藏历,对家堂神的祭祀固定在每年农历的除夕、正月初一至初三、正月十四至十五。祭祀由每家的当家人(皆为男性)主持,祭祀主持者会先点燃柏枝进行煨桑,然后焚烧沿一侧对角线折叠成三角形的白纸与冥币,在祭祀期间他会向家堂神祝祷,祈求家人平安健康。除固定祭祀日期外,若有禳灾祈福需求,也可随时拜祭家堂神。
除每年在各自家堂中敬祀赤沙龙王外,宕昌县新坪村藏族还有集体祭祀赤沙龙王的活动——“七月会”。新坪村藏族称“七月会”为“[tɕɿ pɤ xui]”,“[tɕɿ pɤ]”即“七月”。传说每年农历七月十一,赤沙龙王会回到新坪村巡视,其妻金丝娘娘会在村口迎接他,并一路陪同。巡视完新坪村后,赤沙龙王会去宕昌城区,因为在这几天里,生死簿由他执掌。
同时,在传说中提到的赤沙龙王侧妻“阿麽”,也作为副神出现在当地藏族的家堂神案上,但有趣的是,“阿麽”被单独放置在左上角的独立神龛上。当地藏族村民在向笔者解释这一现象时,皆会使用传说中赤沙龙王强娶阿麽,阿麽对其颇为怨恨遂不愿与之为伍的情节。这种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多元文化间的冲突被演述为了“强娶”外衣下的传说,原本看似不可调和的族群间冲突被缩小为家庭内部矛盾,在这种对“历史真实”的遮蔽下,新坪村藏族与周边族群间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缓和。
三、赤沙龙王传说中的历史记忆
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往往会被不断演进的历史层层遮蔽,它的构建是一种动态过程,而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是静态呈现的。历史实际上具有双重事实,即历史本身和人们对历史或者说历史记忆的记述。前者的本相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能研究的往往是作为“历史记忆”存在的后者,而口头传统作为族群内部保存和传承集体记忆的载体,蕴含着这一族群朴素的历史观。
历史上,宕昌是一个多民族迁徙、混居的地区,作为原住民的古羌人在与其他民族的不断碰撞、融合过程中,已不再是特色鲜明的具有单一古羌人文化因子的族群。在不断演进的历史中,宕昌藏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直处在与周边民族的互动过程中。以人为主体的记述历史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从这一角度来说,是人“创造”了历史,而非忠实记录了历史。对不同文化的吸收和融合重组着宕昌藏族的历史记忆,但人们依旧希冀于从过去中窥见自己来时的路,于是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族群变迁被加以演绎,在族群成员们的集体创作下,成为流传于族群内部的蕴含了自身历史文化信息的传说、故事、神话、史诗等口头叙事文学。
在新坪村藏族中,流传最广的即是赤沙龙王传说。要对这一传说加以分析,并剥离出层累⑬于种种演绎之下的“真实”,提炼出这一传说中的母题是较为可行的研究方法。母题作为“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在于传统中的成分”⑭,在叙事功能方面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母题所承载的信息往往更具可信度。结合当地人将赤沙龙王称为“先人”⑮这一现象来看,赤沙龙王在宕昌地区的活动轨迹极有可能影射了新坪村藏族在历史上的动向。在对赤沙龙王传说做分析后,笔者从中分离出了两个母题——“战争”与“迁徙”。
(一)赤沙龙王传说中的“战争”与“迁徙”
在赤沙龙王传说中,线索清晰的战争共有3场。前两场赤沙龙王的斗争对象为玉帝的太子,即当地传说中的泰山爷黄飞虎,战争结果为先胜后败;第三场赤沙龙王的斗争对象为舟曲地区的喇嘛,战争结果为赤沙龙王败逃。“战争”这一母题的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族群、不同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类的历史即是一部征服史。虽然传说并不具有历史真实性,但构成传说的叙事材料却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来自讲述者们的历史记忆。因此,在解读赤沙龙王传说中的“战争”母题前,需了解这一地区发生过的历史变迁。
传说中明确提到的朝代有两个,分别为唐与宋,对应到历史当中,宕州⑯在唐广德元年(763)因战陷于吐蕃,“吐蕃东进”使这一地区首次受到大规模外来文化的冲击。至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韶收复岷、宕二州。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关赤沙龙王在唐朝的事迹皆由“梦斩泾河龙”变异而来,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段传说是讲述者们为了填补赤沙龙王出身的空白,从而选择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故事移植过来,用以保证赤沙龙王这一形象的鲜活与可信。至宋朝,传说中赤沙龙王的活动范围才真正被限定在宕昌地区。宋以前传说中关于地名和人名的模糊化处理,也进一步佐证了笔者的猜想。在传说中,宋王分封天下神鬼,令赤沙龙王镇守宕昌高庙山,这应当是宕州在北宋时期被收复的影射。
在被吐蕃政权统治期间,宕昌地区番部林立,组织较为松散,被宋朝收复后的第二年,统治者在此设立了宕昌寨,并派官员前来驻守。至南宋,岷州、宕州、叠州、阶州、文州十八番族又降于蒙古汗国。明洪武四年(1371),明将傅友德兵至,西固千户韩文举众归附。明代统治者在这一地区设立卫所,并实行土司制度,宕昌在当时属岷州卫,归卓尼(在今甘南)杨土司治下。可见,受战乱影响,生活在宕昌地区的族群发生着频繁的变动且不同族群间的交往与融合也时有发生。这种历史环境下的动乱成为新坪村藏族口头传说中有关“战争”的历史记忆的来源。
在赤沙龙王传说中,“迁徙”母题实际上与“战争”母题间表现出极强的黏附性。赤沙龙王的两次迁徙皆因战争失败而起,具有被动性。在赤沙龙王的迁徙过程中,“舟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点。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毗邻和民族文化上的相近,宕昌藏族与舟曲藏族间颇有渊源。据部分新坪村藏族村民自述,他们的祖辈是由舟曲的憨板坡(今舟曲憨班乡)迁徙而来。这也涉及新坪村藏语村名的由来,关于这一点,笔者已在前文中做过详细解释,在此不做赘述。
宕昌地区处于东部汉文化和西部藏文化的交界地带,历史上有众多诸如羌、汉、吐蕃、吐谷浑、蒙古、回鹘等族群在此进行势力角逐,造成这一地区的动荡不安。为稳固统治,不同族群的政权皆在此实行过移民政策,同时也有少数族群为避战祸,自行选择迁徙,这些因素令宕昌地区的族群互动显得颇为频繁。总之,受多重因素影响,宕昌藏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其自然人文环境内迁徙流动是经常发生的。
在赤沙龙王传说中,赤沙龙王的行动轨迹为:居于宕昌城内—遭到驱逐—被迫迁往舟曲—再遭驱逐—返回宕昌(村野)。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新坪村藏族将包含赤沙龙王在内的家堂神统称为“先人”,由此笔者大胆推测赤沙龙王的行动轨迹应当是对新坪村藏族迁徙记忆的演述。
同时,如前文提到的,在当地传说中,赤沙龙王是在征得凤凰山神的同意后,才得以驻留新坪村。而当地藏族的神堂主案也皆供奉赤沙龙王一脉的神祇。结合口头传说资料与田野调查实证,不难看出新坪村藏族在迁徙过程中,其信仰也发生了一定变迁。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变迁不仅出于周边强势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新坪村藏族为了消弭与周边族群间的差异而自主做出的文化调试。
(二)结构性失忆中重组的历史记忆
在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中,历史记忆是以该族群所认可的形态呈现并流传的部分,它承载了这个族群的起源记忆和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的族群认同与实际生活中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⑰。
由于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往往会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互动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族群认同的背后也隐藏着文化资源的争夺与统治权力的博弈,因此族群的身份并不能被简单地标签化。当族群认同发生变迁时,人们为了解释这种变迁的合理性,会主观地对自身“历史”进行建构,使其与当前的现实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历史记忆被重组,尤其是在移民情境之下,结构性失忆更容易在族群内部滋生,在动荡中增强族群的向心力成为人们重组历史记忆的动机。
新坪村藏族作为曾有迁徙史的族群,其生存空间在与其他族群的冲突中被压缩至雷古山脚下的深沟中,汉民族文化也长期对他们造成影响。如何保证族群内部的凝聚与稳定并与周边族群和谐共处,成为新坪村藏族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一需求下,新坪村藏族在保留了“战争”与“迁徙”记忆的前提下,让与周边汉民族文化有着亲和力的赤沙龙王成为族群的代言人,并试图从流传度甚广的《西游记》中为赤沙龙王寻得一个不容辩驳的正当身份。
在赤沙龙王传说中,明显可见其与泰山爷所代表的汉族、阿麽所代表的舟曲藏族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或为战争、或为联姻,皆体现出多元文化间的碰撞、冲突与融合。费孝通指出:“所谓文化的概念,说到底是‘人为、为人’四个字。”⑱“人为”意为文化由人创造,“为人”意为文化的功能在于满足人的需求。新坪村藏族之所以能将周边族群的“多元”吸纳融合成为“一体”,在于他们选择性接受了周边多元文化中能满足自身需求的部分,即在维持族群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尽可能弥合与周边族群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减少冲突的发生,以此来保证族群的稳定发展。
结语
赤沙龙王传说是糅合了“梦斩泾河龙”的故事与新坪村当地口头传说的产物。作为一则信仰传说,它解释了当地赤沙龙王信仰和新坪村“七月会”的由来,以及为何会有妇女“骂神”仪式的原因。由于口头传统是存在于民间的,不易被社会权力操纵的叙事,因此它暗含了更为隐秘的历史记忆。赤沙龙王传说不仅保存了新坪村藏族的移民记忆,也影射了这一族群在历史上与周边族群发生的种种互动。这也证明,赤沙龙王信仰有效弥合了新坪村藏族与周边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和谐共存,保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和谐发展。
作者简介:杨明明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与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