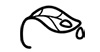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胥志强
作者:胥志强  创建时间:
2024.01.11 12:50:00
创建时间:
2024.01.11 12:50:00
【摘要】中国思想对礼、俗的关注始于2000多年前,而且是一个高度成熟、持续的传统。但在晚清礼教批判的背景下,现代学术史中的礼俗研究始于以俗释礼与俗的上升,这一开端引发出两个发展方向:一方面是现代民俗学更彻底地解构礼的神秘性,最终使得礼、俗越出礼学视野,均成为民俗学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礼学也在部分接受俗的维度与现代意识,同时积极寻求回应时代问题与西方学术,结果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礼俗学”的成立,以及“新礼俗”构想的出现。这种相互竞争、吸收的态势持续至今,但古典礼学明显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势出现,它通过对传统的解释学重构,针对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危机,阐发出了一种朝向当下与未来的礼俗学视域。这样,现代礼俗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或解释的循环过程。重审现代礼俗研究的学术脉络,对于中国民俗学话语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礼俗;礼俗学;以俗释礼;礼俗互动
“礼俗”一词由来已久,最早见于《周礼》,如《天官·冢宰》篇曰:“以八则治都鄙……六曰礼俗,以驭其民。”①“礼俗学”一词,则由现代学人邓子琴所创,是指“讨究礼俗一切内容,因以指导吾人生活之学。盖学而兼术,知识的而又兼规范的者也”②。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关于民俗的思想,实际上是围绕礼或礼学展开的,如张紫晨所说,“我国民俗学理论的开始,是与礼的理论同步的,是混而为一的……中国的俗在两三千年前便纳入礼的轨道,因而关于民俗的理论,也便孕育或包含在礼的理论之中”③。因此,邓子琴所谓礼俗学,也可称为中国传统民俗学或民俗思想。但在礼学中,礼毕竟是支配的,俗是从属的,因此并无礼俗并称之学;经过清末民初礼教批判之后,俗才浮出礼学话语的表面,所以礼俗学本身也是现代观念的产物,而且是礼学衰微、边缘化之后的产物。现代中国民俗学主流的理论方法是来自西方的,但作为一种延续3000多年的学术思想传统,礼俗学本身并没有在现代消亡,而是以一条伏线长期存续,近来甚有浮出地表之迹。本文的任务,即是尝试勾勒礼俗学从清末至今的发展脉络,总结这一中国传统民俗思想的现代命运,以探求中国特色民俗学话语建设的理论视角。
一、以俗释礼与礼学视野的崩解
如前所述,礼俗学是既传统又现代的产物,所以其诞生于那些具有一定现代意识与民主(民本)思想的学人。早在19世纪80年代,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礼俗志》已经透露出新的气象。黄氏能客观看待各国礼俗的不同,认为“异者,礼之末;同者,礼之本”④。同是因为“天之生人,耳目口鼻同,即心同理同。用礼之节文以行吾敬,行吾爱,亦无不同”⑤,异是因为人情即习惯使然,所以“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引人情而为之者也”⑥。这种分析就完全不同于对礼的理学或形而上学式解释,而是试图从人的方面来释礼——“习惯之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是故,先王之化民,亦慎其所习而已矣”,当然也同时保留了礼学化民成俗的传统观念⑦。20世纪初的礼俗论述,实际上延续着这一趋势,即突出俗的正当性。1905年,刘师培在《礼俗原始论》中援引西方人类学视角来解释冠婚丧祭等上古礼俗的起源,从而证明“上古之时,礼源于俗,典礼变迁,可以考民风之同异,故三王不袭礼”⑧。到1910年张亮采编纂《中国风俗史》,可以说俗已经成为相对于礼的专门知识领域了。他在《序例》中说,“《记》曰:礼从宜,事从俗。谓如是则便,非是则不便也。圣人治天下,立法制礼,必因风俗之所宜。故中国之成文法,不外户役、婚姻、厩牧、仓库、市廛、关津、田宅、钱债、犯奸、盗贼等事,而惯习法居其大半。若吉凶之礼,则尝因其情而为之节文。无他,斯于便民而已”⑨。这就大大强调了风俗之宜在制礼中的地位,是对俗之相对独立性的理论辩护。当然,全书思路仍在礼学之范围中,因此本书中的“风俗”是与礼教相对而言的,与今天理解的“民俗”相差甚远。如作者自述其写作动机为:“亮采夙有改良风俗之志,未得猝遂,乃以考察为之权舆。又以为欲镜今俗,不可不先述古俗也。”⑩胡朴安等编写的《中华风俗志》的意义与性质与此类似。如许世英在该书序言中说,“中国风俗,古无专书”⑪,胡氏的开创性即在于编写了第一部系统的风俗志。张紫晨也指出在该书的“民俗志述中重要习俗尽皆有之,同时对奇俗、杂俗、异俗也有注意,特别是陋俗、迷信更是遍于各卷。这大约是辛亥革命以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洗礼,眼界与思想均有不同”⑫。当然,该书同样保持了礼学旧传统,甚至更为保守。
与上述论著尚保持部分礼学视野不同,新文化运动中儒学、礼教受到激烈批判,此后的礼俗研究一方面延续了之前发扬俗的趋势,但最终脱离了礼学视野。1924年,江绍原与周作人以礼部总长、次长相谑,在《语丝》发表大量古代礼俗迷信的研究。他质疑周作人所谓(道学家之前的)“本来的礼”是种理想化,同时指出,“研究人类学的告诵我们,世界各处的野蛮民族,几乎个个有或种的礼和乐;野蛮人自生至死,几乎天天事事要受‘礼’的支配……野蛮人的礼,的确是文化的复体:若用我们的眼光去分析,其中至少有我们所谓的‘法术’(Magic)的分子,宗教的分子,道德的分子,卫生的分子,还有艺术的(狭义的)分子。我信中国真正‘本来的礼’,也是如此”⑬。进而建议,“研究者应该把礼俗的界限打破……古俗有一部分见于著录,因而得了古礼的美称,成为后人们的叹赏,保存的对象。然没有这样幸运,久已夫湮没无闻的古俗,正不知有凡几,虽则这一部分古俗中应有一部分至今尚以或种形式流传于民众间。故不但古礼与古俗不可分为两事,即古礼俗与今礼俗,亦不应认为了不相干的两个研究区域”⑭。总之,“要研究‘先王’、‘先民’的生活思想习惯,最好多多参考愚夫愚妇、生番熟番们的言行”⑮,这就彻底打破了礼学的支配性视野。
到1930年李安宅《〈礼记〉与〈仪礼〉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这一路径已经全面展开。他以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对两书中的礼论进行批判,“使这两部书顿然失掉了它们历来保有的神秘性,由着圣人的天启,降到社会的产物”⑯。又秉持文化人类学的立场,认为“‘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原来作为经典的两礼,现在只具有社会学材料的价值,而被“穿插在文化之‘普遍型式’(universal pattern)的范畴里”了⑰。
与此书类似的还有杨树达1933年出版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在其中礼学话语只剩了历史材料价值,杨氏特从历史记载中发掘俗甚或背离礼的一面,也已不再作出褒贬、辩白⑱。而瞿兑之1928年出版的《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更进一步,批评传统历史书写“详于帝者上仪之盛,而忽于人民日用之常”,有政府之制度史而无社会之制度史,所以他论述婚丧就不涉礼制而只呈示民之“常行”了⑲。在这一趋势之下,礼学自身的视野消失殆尽,颇有庄子所谓不见“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之态势。总之,清末以来礼俗讨论大背景,上承晚明以降的礼教批判,俗的一面被挖掘而上升。礼俗之间原本有如万有引力相互牵系,此时俗的一方加速逃逸,最终脱离礼的轨道,至现代民俗学、人类学引入后,只剩下了历史与资料价值。这种趋势,持续至今。
二、礼学的回应与礼俗学的萌芽
但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礼俗话语不仅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重新出现,而且在学术研究中开始回应现代生活与西方民俗学范式,“礼俗学”以纲要的形式首次成型。社会实践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对礼俗的挪用或化用。礼俗在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以至整个社会学说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既是他分析中国问题的价值出发点(所谓“文化失调”),也是社会建设的理想之所在(“新组织即一新礼俗”)。以此为核心理论构想乡村建设,其实际效果如何,已为历史所证明。另外,梁漱溟对儒学与传统社会的认识过度理想化,自不待言。但他在呼应时代问题与西方思想中酝酿的新礼俗理论,仍然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在新文化背景之下,他也不能不承认明清以来儒学内里空虚与礼教的锢蔽,主张“非彻底把假道德(礼教)无真力量而表面只剩躯壳的东西毁完再生新的不可”⑳。其次,他反思了现代西方理论对于社会秩序构想的不足,发挥了礼俗视野的新意义。这表现在,一方面,现代“国家乃只管人的生活,不复问其生活之意义价值”,而“所行之法律制裁的方法,实以对物者待人”,也就是只知满足欲望,而不知人生尚有“向上无尽之开展”的一面㉑。另一方面,他援引杜威的发现指出,现代社会缺乏“社会的精神”,也就是交流与情感,这恰恰是礼俗传统所强调的。由这两点出发,他理想中的新社会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这只能是由礼俗而非法律或政治所能达成的,所以他深信礼俗传统具有普世意义,“在近代法律制度后,更进一阶段的文化便是礼”㉒。这些论述可谓有的放矢,不无启发意义。
另一值得注意的礼俗实践出现在国民党政权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华民国礼制”制定这一背景。关于这一运动的意义与性质,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虽然这种礼教的哲学意义是混乱的,几乎不值得讨论,但是其政治社会意义则是足够清楚的,而且是颇值得注意。一直被真正讨论的东西是保证社会稳定和民众纪律的手段。在国民党的思想家看来,儒家学说是为了达到此目的由人类设计的最有效、花费最少的统治工具。”㉓但这一官方行政活动也催生了一些讨论礼俗的学术成果,主要是缪凤林、柳诒徵与陈果夫在“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上关于礼俗的讲座。缪凤林的《中国礼俗史》(又名《礼的研究》)㉔实际上是其文章《谈谈礼教》㉕的扩充,所以论述基本未涉及俗,只是从传统“礼学”阐发礼的定义、范围、建立(起源)与功用等问题,原文仅20余页,且立场保守,无甚新解。陈果夫的讲稿《中国礼俗》㉖(后有单行本《中国礼俗研究》)却是名副其实的礼俗讨论,而且他理解的礼俗,并不偏重礼的方面,而是与风俗、民俗混用,更贴近俗的方面与现代民俗学视角。所以他从文化需求角度解释礼俗的起源、演变:“礼俗的产生,都是为着适应生活的需要,看了需要,才有发明。”㉗而且他更多从客观角度看待中国礼俗的特点,如多元化、农村化、家族化、伦理化等。陈氏的礼俗研究服从于其制礼的动机,从其政治立场与时代背景出发,强调了新礼俗的民族意识与秩序意识,这两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岁时风俗的关注,此后与邱培豪合编的《中华国民生活历》实际上是以岁时为序构造的一个想象的风俗共同体㉘。
柳诒徵的讲稿《礼俗史论略》(后以《中国礼俗史发凡》为名发表)的文化立场同样保守,但不是纯然礼教的视角,而是首次阐发了传统礼学中礼俗互动之义。他指出,“世言治礼,皆知宗经,经即史也”,从方法论上指出了时俗在礼教中的地位,所以“言礼而不言俗,未为知礼”㉙。他也认为礼起于俗,但不同于江绍原等人的看法,保留了礼的权威性:“礼俗之界,至难划分。笃旧之士以《士礼》及《周官》所载,皆先王之大经大法,义蕴闳深,不可以后世风俗相例。究其实,则礼所由起,皆邃古之遗俗。后之圣哲,因袭整齐,从宜从俗,为之节文差等,非由天降地出,或以少数人之私臆,强群众以从事也。”㉚所以,“礼非尽循俗也,俗之甚敝,不可不革,而又不能尽革者,则有礼以适其情而为之坊”㉛。因注重礼俗间的这重关系,所以柳氏的观念较为通达,如他认为,“有后世之俗胜于古礼者”㉜,以为蜡祭、赛会也反映人性的张弛之道。他对古代礼俗的理解也较为理想化,“古礼之协于人情,合于民治,其精奥赅备,固非徒执臆见近事所可测定”㉝。当然这也可视为阐发原初礼学的理想之义,如他批评宋明儒者“其于化俗也,尤形扞格,流俗至以其讲道德而避之而侮之。盖古有乐教,故讲道德而宽裕安和,行之不形拘苦。后世无乐教,故讲道德而鞭辟强制,行之鲜获同情”㉞。至此,柳诒徵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礼俗论”大纲。
邓子琴的著作《中国礼俗学纲要》在立场上与柳诒徵相近,也是“以中国文化观点而治礼俗”㉟,但篇幅大大超过柳著,更为详细地讨论了礼的含义,礼与风俗、民俗概念的区别,礼俗的起源、意义、变迁以及与伦理的关系,研究礼俗的方法等相关问题,是为中国礼俗之学的第一次系统性阐发。邓子琴的一个重要贡献,还在于首次对传统礼俗学与现代民俗学的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比较。他指出,西洋之研究民俗,旨在求真,而中国自昔之研究民俗,旨在求是,“求真固用客观的态度,利在分析比较。求是故必参以主观见解,利在浑括指示”㊱。表现在各自的概念上,民俗“为感情之活动,为不自觉之惯习。(亦可云无意识之行为)”㊲,礼俗“即可谓自觉的关系,(亦可云有意识之行为)”㊳,换句话说,“凡觉醒的习惯(即有意义的之行为,为理智或本心所指导发出者),构成一定之仪式,而流行于一般社会中者,谓之礼俗”㊴。而“风俗”也是礼俗传统中的概念,“风俗范围广,而礼俗范围狭。其在古代,言风俗者,殆无不包括礼俗。风俗一名,亦较礼俗为常用。凡总括一地域或一时代人民生活之一切现象,而以价值意义评判之者,谓之风俗”㊵。这样,中国礼俗和礼俗史就不再是西方民俗学的材料,而是具有自身独特视角的学术概念,邓子琴初步树立了中国礼俗学的独特视角,在现代礼俗学的发展中意义重大。
三、传统文化热与礼俗现象的再承认
但此后几十年,礼俗学以至民俗学研究都归于沉寂,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恢复。此前学者何联奎著有《中国礼俗研究》(1983)一书,从人类学视角讨论中国古代礼俗,延续的是江绍原、李安宅的进路,对传统礼俗本身未有进一步的发挥㊶。1990年,杨志刚在《礼俗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礼俗在中国文化中耦合成一个特有的系统,发挥极重要的功能,并以矛盾运动的态势影响和制约历史的发展”㊷,所以礼俗研究不能着眼于事项,而要进行深一层的发掘。在20世纪90年代传统文化热的大背景中,礼俗传统与思想重新进入学术视野。1993年,王贵民的《中国礼俗史》与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学史》出版,从不同角度重新发现了礼俗思想的学术意义。
王贵民明确指出礼俗一词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确切的词汇,一个科学的概念。“‘礼’是指所行之礼,由此而形成的礼仪,制定的礼制,乃至解说礼的理论都是;而‘俗’则是人们习惯所衍成的风俗或者说习俗。历史地看,人们生活中某一活动形式,反复行之,浸久成俗;‘俗’一旦形成之后,在上的采风者、制礼者认为是良风美俗,就给予一种有意识的规范,这时就成为‘礼’。可以说,前者叫作‘约定俗成’,后者就可以称之为‘俗定礼成’。‘礼’成之后,在履行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加入某些新的‘俗’。这样,礼与俗就是一种相互吸收、结合的运动形式。”㊸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与俗关系的准确阐述。而“礼俗”是指用教化的观念规范过的风俗,凝结为一定的形式即“礼仪”,此外还有许多风俗无须或未曾被规范,保留了自然的特色,也就不具有礼俗的性质。这就科学、严谨地区别了这几个长期众说纷纭的概念。王氏继承了近代以来的礼教批判思想,因此在立场上与柳诒徵、邓子琴等具有很大的不同。他指出礼俗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历代朝廷都要创作礼制,事实上就是因俗成礼,或者是援俗入礼,从而以礼制俗。所以,礼俗偏重于礼制的内容,它把风俗中一些生活习惯、社会交往和鬼神信仰等等外在的行为,都纳入礼制中,使之‘咸归于正’,也就是使一般风俗加进了理性的因素,实际上也就加进了人为的强制力量。因此,礼俗以风俗为基础,却有异于并反作用于风俗,礼俗使风俗条理化、统一化,也带来了凝固性和保守性”㊹。另外,王氏理解的礼俗之范围已经大为缩小,已不是宏阔的一切政教、文化,而是一方面限于“礼仪”,另一方面限于民众的“俗礼”“幼礼”,尤其是加入了不为礼教所重视的人生仪礼(生育、养老、岁时等),显示出现代民俗学的影响。
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学史》主要是从现代民俗学的视角挖掘古代文献中的民俗与民俗记载,所以其取材范围不限于“风俗”与风俗志,而是扩展到月令、农书、占经、方言等著述。但在论述先秦诸子、汉魏学者以及明清作家的“民俗观”时,“不自觉”地呈现了传统的民俗思想或礼俗学视野。比如他注意到:“《周礼》记述习俗不是按照民间原俗述其原尾,而是把它提高,加以规定和系统化,并在详细分工基础上设官管理。这就使民俗与礼制结合,造成了中国社会俗与礼,礼与俗的特殊关系。……这是中国民俗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民俗既经纳入礼制,成为王室和政体中的一种法度,其地位便很不相同了。由此,礼俗问题,便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成为从天子王戚、高官显宦,以及文哲儒士都不能等闲视之的重要事项了……《礼记》面向庶人讲礼,少以王事为论,把‘礼’的思想推广到平民群众之中。”㊺这就深刻地把握了中国礼俗的发展趋势。如前引所示,张紫晨认识到我国民俗学理论与礼的理论的混而为一,关于民俗的理论蕴含在礼的理论之中。他认为:“在先秦时期,单纯的礼,单纯的俗是不存在的。”㊻另外,在武文主编的《中国民俗学古典文献辑论》一书中,尤其第一章“民俗思想”遍采经史子集中关于礼、俗的一般或具体论述、思考,客观呈现了中国古代礼俗理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虽然体例未备,但对于阐发古代礼俗思想,学术参考价值极大。㊼此外,尚有若干博士学位论文、论著涉及古代民俗思想,但大多对礼俗学视野本身注意不足,此不赘述。
张紫晨的著作对后世礼学思想对于民俗的解释及其影响讨论很少,尤其忽视了宋明之后礼教下移背景出现的礼俗或民俗观,以及礼教批判思想对于民俗的论述。关于这一点,蔡尚思的《中国礼教思想史》一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该书可视为是中国2000多年的礼教思想斗争史,尤其从哲学史的高度厘清了宋明之后礼教异化的思想根源,以及从李贽、袁枚到今人陈独秀、赵纪彬等人对于礼教的思想批判,虽然并非专门的礼俗思想史,但也重申了现代民俗学的这一起源语境㊽。这一点也与现代民俗学史的研究形成了某种呼应。赵世瑜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指出,中国自身研究民俗的传统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民俗学倡导者的许多思想“与以前两三百年来的思想发展有极深的渊源。在倡导‘个性解放’方面,周作人明确指出自己与晚明时人的共性;‘打倒孔家店’与晚明以来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关系极大;顾颉刚也说自己的‘疑古’受到清代姚际恒、崔东壁等人的启发”㊾。显然新文化运动主要发扬了批判的一面,但他认识到中国传统学术对民俗的重视中,还包含许多宝贵的思想,如民主意识、致用精神、实践意识等,“对这条线索的彻底清理,还有待于有志者的继续努力”㊿。稍后学者周志煌在其博士学士论文中,进一步阐明了现代中国民俗学发生的传统学术背景,“就纵贯的学术思想发展来说,一方面它继承着经学传统不断失落的过程,从乾嘉学术、宋学、晚清金文学派不断以‘史’来挑战‘经’,代替‘经’的神圣地位的思想转变,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清中叶以降,知识分子以先秦诸子来反对儒学定于一尊,试图‘通经致用’的努力”;“换句话来说,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所承接的是儒学的‘去中心化’,而次属于‘经’的‘史’‘子’进入中心的过程,即使原属于儒家精英视为外来宗教的佛学,也开始进入学术中心的位置而进行研究”51。总而言之,这些研究说明,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与取向并未彻底脱离中国传统民俗学或礼俗思想的大视野,只不过其偏重继承的是礼教批判或为俗的正当性辩护的这一脉。
四、礼俗思想自身视角的再发现
新世纪之交民俗学史研究的确认,以及此后大量礼学相关研究论著的出现,显示着礼俗传统正在重回学术视野。但对于礼俗学的理论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成果出现在哲学界而非民俗学中。一些持儒学立场的学者开始介入传统礼俗复兴的反思甚至实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人为张祥龙。除了对儒学、礼乐文明的一般性辩护外,他对具体礼俗现象也有讨论。如在《中国的节日在哪里?》一文中,阐发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含义与意义,发出了“中国人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节日”的呼吁52。更有甚者,他参照《仪礼》《礼记》与《朱子家礼》中的古代婚礼仪节,依据“昏义”制作了一份“儒家当代婚礼仪式”,反映出传统礼学重新切入日常生活的趋势53。但如上述考察所示,在经过百年的礼教批判与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礼学与礼俗很难实现直接的“复兴”。因为今日的情境已经不是“礼崩乐坏”,而是传统礼俗思想本身的崩坏。传统礼俗学的本质是什么?意义何在?它如何正当地切入现代生活?这构成了晚清以来始终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的棘手问题,也需要一些根本性的解答。所以,一些持传统文化立场的严肃学人,选择从哲学进路,对古代礼俗传统进行彻底的重释,其中陈赟的相关论述最值得关注。
古代思想的核心精神与视野何在?它如何对现代人有意义?陈赟关于礼俗传统的论述切中了这些核心问题,重新从古典视野出发解释了习用的“政治”“教化”“礼乐”“风俗”这些关键概念。他的理论出发点是对“政治”之含义的“拨乱反正”。他指出,政的本义是正,“在《论语·颜渊》中,孔子以正来规定‘政’,《管子·法法》亦云‘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正定万物之命,也就是物各付物(庄子所谓‘齐物’),把生命还给生命”54。各正性命,也就是每个生命各个实现其价值、天命。而这除了个体的责任之外,还需要一个得以发生的境遇,而为政就是“着力于营构这种境遇,以为各正性命开通道路”55。总之,古人理解的政治或理想的政治不是现代人理解的斗争的场域或纯粹的权力,“治理活动的本质是将天下归还给天下,将生命归还给生命”56,“必须作为开发人性的可能性的文化事业来加以确立”57。
而礼或礼乐也就是各正性命的一种方式,诚如《左传》中所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成公十三年)58,“人只有在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也就是人文化的身体中方能贞定自己、正其性命。这实质上是‘文之以礼乐’(以礼乐文身)的过程,将身体展开在礼乐中”。礼乐要完成这一文化功能,就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即“一切文化(例如法则、制度、风俗等等)的建造,都既是人性的可能性的打开,也同时是天命的接纳与推进”59。“教化”的意义与原则也是在这一理论视域中出现的,“一切类型的‘人文’(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学、艺术,等等)都必须被理解为‘教’,也就是‘文化’‘教化’‘教养’‘养育’的方式,作为这样一种方式,它是否有助于培植真正的人性,才是对它的正当性的考虑标准”60。这一论述意在避免如现代文化人类学对礼俗理解的那种粗率的文化相对论与空泛的需求论,也避免将教化等同于那种戕害人性与生命的“礼教”或意识形态。
那么“俗”的位置或正当性何在呢?陈氏延续了现代学者发扬的“礼从俗”这一路径。他首先指出,在古人的视野中,在地方性的或具体生存环境中出现的俗已经是一种贞定性命的方式,“正如慎子所云‘礼从俗,政从上’,礼作为生活与居住的法则,发现于本地方的自发‘化生’的‘风俗’,这地方性的风俗,就是伦理(礼)借以展开自身的方式”,也就是在起源上已经是天地所“化生”61。所以礼必须尊重地方性的习俗或习俗的地方性:“作为在地性的生活方式,风俗乃是天地之化流行于人而日生的天命,以及该地方的人们定其命的特有方式。当《礼记》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时候,基于地方视野的政教原则已经贞定,这就是它不是建立在地方之外,而是发现在地方之中,它体现了对地方性居住样式的真正尊重。这样的政教原则展开为伦理,作为伦理的具体形态的礼不同于风俗,它立足于风俗,但同时又是对风俗的移易与转化。”62那么礼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介入、移易俗呢?“礼,它导生于地方性的风俗,然后它又是地方性风俗的守护与提升。在礼中,地方作为地方而得以敞开,而且,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居住方式得以相互通达。伦理超越了地方,它又把不同的地方作为它们自身而敞开。”63换句话说,礼作为为政者的行为,侧重的不仅是地方性的成立,更是不同地方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这一解说颇类似胡朴安的观点。胡氏说,各地风俗不同,未有如中国之甚,但数千年来,“在统一国家之下,卒能相互维相持于不敝者,其道安在?”,他认为原因是“盖以学术统一而已矣”64。这个“学术”准确说应该就是礼。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齐一风俗、移风易俗不是或不能是驱逐地方的过程,而需要“敞开了地方性,同时也敞开存在的具体性”。总之,古人所谓的政、教、礼、俗都应该是让“存在者各以自身的方式正其性命的过程”65。这其实是一个极具现代意识的解释学重构,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间”意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总之,21世纪以来的礼俗哲学论述,对古典礼俗视野进行了更深刻地阐发,对现代性在学术、实践上的诸多预设构成了深刻的挑战,对礼俗学研究以及民俗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当然,如何实现哲学与民俗学的对话,还是一个有待持续展开的任务。
结语
中国思想对礼、俗的关注始于2000多年前,而且是一个高度成熟、持续的传统。但在晚清礼教批判的思想背景中,现代学术史中的礼俗研究,始于以俗释礼与俗的上升,这一开端引发出两个发展方向。一方面是现代民俗学更彻底地解构礼的神秘性,最终使得礼、俗越出礼学视野,均成为民俗学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礼学也在部分接受俗的维度与现代意识,同时积极寻求回应时代问题与西方学术,结果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礼俗学”的成立,以及“新礼俗”构想的出现。这种相互竞争、吸收的态势持续至今,但古典礼学明显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势出现,它通过对传统进行解释学重构,针对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危机,阐发出一种朝向当下与未来的礼俗学视域。这样,现代礼俗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或解释的循环过程。
在当前非遗等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中,重审传统礼俗思想的视野,对于中国民俗学相关学科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礼俗学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传统,总结其性质与意义将是一个需要具体展开的任务。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礼俗传统与中国民俗学理论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YJC850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胥志强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神话学。